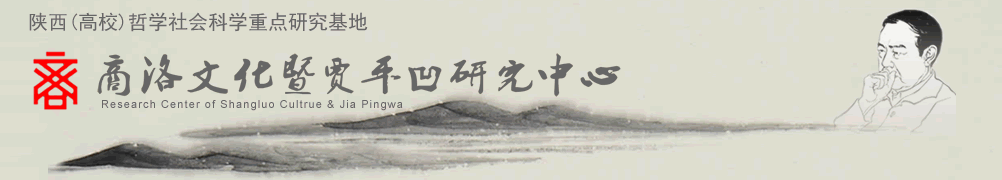邓晓芒/文
从表面的思想倾向上说,王朔和张承志似乎是对立的两极,前者是看破红尘后与世俗同流合污、痞,后者是坚持最彻底、最纯洁的道德理想,是极端的纯情。然而从精神实质来看,他们两人却有着原则上的根本的一致,即他们都想完全无保留地使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与最底层的民众融为一体。这与“红卫兵精神”、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使一种图腾式的大众崇拜戴上了大众固有的痞性。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一向都具有一种“民粹”意识,它历来主张知识分子要懂得民众的疾苦,成为民众的代言人和救主。正如当年的“民粹派”到民间去穿草鞋、吃粗粮、干农活一样,“五四青年”到农村去,60年代上山下乡,“文革”的发动群众、忆苦思甜,结果使知识分子不但大众化、平民化了,同时也痞子化了。王朔难道不是知识分子、文化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模范吗?当代痞子文学只不过是首肯了这一方向,主张要想为民众说话,首先要放下架子,自己成为地道的民众,即最底层的痞子,就要说痞话。一切社会都有痞子,但中国的特点是痞成为通行的规则(尽管痞本身意味着无规则、胡来、原始自然)。所以王朔在痞时感到自己真正纯洁,他回归到了自然本性。张承志同样拒斥对这自然本性的一切文雅和教化的提升。当代中国人的灵魂在挣扎中左冲右突,最后总是回归到原始和儿童的纯真。人们说,王朔使人感到自己成了动物。真是这样吗?非也!王朔把人的动物性的痞理解为纯情,这无异于一种自欺。人要真感到自己成了动物,他会有种内心本真的痛苦。王朔却感到怡然自得,超然洒脱,自我欣赏,以为这才是人的真性情,才上升到了老庄和禅悦的境界。这只是一条自造的逃路,他的无出路正在于没有异化感,没有要拜托非人状态的内在冲动。人们又说,张承志追求的是“清洁的精神”。真是如此么?非也!张承志把人和动物之间的生存状态作为精神保持“清洁”的条件,这种精神拒绝和害怕一切文化的发展与成熟,逃避人的生活世界。这是一种停滞、倒退、心怀嫉恨的精神,一种遏制精神的健康发展的精神。他的无出路在于这种精神骨子里的反人文性和自我毁灭性。世纪末的中国人,要寻找的绝不是这样的灵魂。
由此可见,王朔和张承志所表现的,是痞和纯情的两种不同的结合方式。他们各自立于自身的立场,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和对方的立场已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各有自己尚不彻底、尚未看透的地方。真正看透了中国人的人心、人性的,是贾平凹,特别是他的《废都》。
一
贾平凹80年代即以他的“商州系列”作品在中国新时期文坛上雄踞一时,人们欣赏的是他在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文化味”。它是“地方的”,但却是大地方,是其他一切小地方的发源地和根。它既不同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浮光掠影的理想追求,也不同于对大众生活的如实反映,而似乎是深远久远的历史本身在现代发出的沉闷回音。他对历史掌故、乡土风俗和民间禁忌、国民心理的韵味理路的熟悉程度及生动描绘,是超出旁人之上的。然而进入90年代,他忽然有了一番深沉而痛苦的反省,想起“往日企羡的什么词章灿烂,情趣盎然,风格独特,其实正是阻碍着天才的发展”,而自己已到了40岁,“舍去了一般人能享受的升官发财、吃喝嫖赌,那么搔秃了头发,淘虚了身子,仍没美文出来,是我真个没有夙命吗?”(《废都·后记》,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519—520页,下引此书至注页码)他发现自己“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第520页)。于是,当他要在“生命的苦难中”、在这部40万字的“苦难之作”中来“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第527页)时,他便失去了以往的宁静、隽永和娓娓道来的文风,变得慌乱而急促;当他下决心要切实地通过写作来寻找自我、把捉自己的灵魂时,他看到的恰好是自己的失落,即失了魂;或者说,他发现原先自以为圆满自足的那个自我只是一个假象,他的真我其实是分裂的——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庄周还是蝴蝶了。
小说的主人公庄之蝶,曾经是一个真诚、纯洁的青年,12年前曾与本单位一位女性景雪萌恋爱,竟“数年里未敢动过她一根头发,甚至正常的握手也没有”(第66页);后来另娶了一位名门闺秀牛月清。成了知名作家以后,在西京城里地位极高,是文化界“四大名人”之一,市人大委员,人人都以能一睹容颜为快,真是如鱼得水,要什么有什么。然而,正当他功德圆满、辉煌灿烂之时,他却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他看透了知识界文化界的无聊和空虚,识破了一切官样文章和纸糊桂冠的虚假;但他并不像王朔那样愤世嫉俗、倒行逆流,而是“大隐隐于朝”,逢场作戏、以雅就俗。他深知自己早已丧失了一切理想主义的道德信条,但他无法起来指责任何人,因为这个社会的堕落也正是他自己的堕落,他就是这个沉沦着的社会的典型代表和“精英”。因此他唯一能做的和想做的只是充当这个已经腐朽了的伦理体系身上的蛆虫,寻求着这个封闭的实体上的裂缝和“破缺”(第29页),以维持自己那尚未被窒息的最后一点原始生命力;用孟云房的话说就是:“一切都是生命的自然流动,如水加热后必然会出现对称破缺的自组织现象”(第30页)。当然,这种伦理体系上的“破缺”现象主要集中体现在爱情或性关系上。庄之蝶身为名人,有那么多人读他的书,据说他的书又尤其写女人写得好,身边自然就聚集拢来一批女性崇拜者。这些女子一个个形容姣好,聪明伶俐,风情万种,善解人意。她们仰慕庄之碟的知识、文化、气质和艺术家作派,更陶醉于他作为一个性伙伴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这是一个真正的“自然人”,他不做作,不虚伪,遇到一个灵动的女子,他总是能够做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并顺顺当当的成其好事。不是凭他的外貌(他的外表很一般),也不靠花言巧语,更不凭借暴力,而只凭他一腔诚心、真心,他便同时占有好几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这简直就是一个使男人暗中羡慕的当代贾宝玉。
因此,现实中的庄之蝶尽管显得那么玩世不恭,整个一个玩弄女人的痞子,但在理想或梦幻中庄之蝶却自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天才,能将除去一切道德面纱的赤裸裸的痞性、兽性变得如此优雅和温情,甚至使之显出一种自然天成的纯洁和美来。当然,这种美决不是精神上的,而是一个有精神的人对肉体的崇拜和迷恋,是精神的颓废和沉沦。当精神无论如何也看不到自己头上的天光、无法引导自我超升至神明般的至福境界时,唯一能使灵魂感到“安妥”的便似乎是向肉体沉沦。这种沉沦是如此惬意、如此甜美,毫无罪恶感和触犯天条的恐惧,因为精神的唯物主义知道,没有上帝,也没有死去的灵魂。人生如过客,如蛆虫,亦如梦幻。而最真实的梦幻是蛆虫的梦幻,只有蛆虫的梦幻才使得蛆虫不只是蛆虫,而有了“文化”,成了天道和自性。可见,理想和现实、精神和肉体、梦幻和蛆虫毕竟还不是一回事。精神对肉体的崇拜虽不是“精神上的”但毕竟是“精神性的”,亦即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最高级的文化,否则庄之蝶和那些无知无识的流氓没有区别了。庄之蝶并不屑于普通诱奸者的禽兽行,他向来看不起杯水主义,他是怀着一腔纯情的真诚去和人通奸的,他痞的潇洒,痞的有水平。他水性杨花、随时可移情别处,但每次都忠实不渝,全心投入。孟云房说他“别人外面玩女人都是逢场作戏罢了,庄之蝶倒真的投入感情!他实在是个老实的人“(第480页)。他要天下一切美妙女子,但只是为了将自己的纯情无私地赐福于她们,因而一点也不显得“个人主义”、可是到头来,他把这些普通女子从粗痞提高到“纯情”的层次上来、因而“造就”了她们的同时,也就将她们毁灭了。正如柳月说的:
“是你把我、把唐婉儿都创造了一个新人,使我们产生了重新生活的勇气和自信,但你自后又把我们毁灭了!而在你毁灭我们的过程中,你也毁灭了你,毁灭了你的形象和声誉,毁灭了大姐和这个家!”(第460页)
这些女人,虽然庸俗一点,可都是些好女人,即使有些越轨行为,也是在压迫下的自然反抗。如唐婉儿跟周敏私奔,阿灿不惜卖身而给妹妹报仇,柳月看孩子给吃安眠药,都是情有可原。但她们都并不觉得理直气壮。一旦遇到了庄之蝶,他们就一个个忽然都鲜活起来,迎风招展起来。是庄之蝶给了她们精神力量,使她们看到人生中还有些可以问心无愧的追求东西、新鲜诱人的东西,但又是绝对高级的东西,因而都死心塌地的跟了他,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精神王国中的奴隶和泥土。唐婉儿曾激情洋溢地对庄之蝶说:
“我想嫁给你,做长长久久的夫妻,我虽不是什么有本事的人......但我敢说我会让你活得快乐!因为我看得出来,我也感觉到了,你和一般人不一样。你是作家,你需要不停的寻找什么刺激,来激活你的艺术灵感”,“我相信我并不是多坏的女人,成心要勾引你,坏你的家庭,也不是企图享有你的家业和声誉......不是的,人都是追求美好的天性,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喜新厌旧是一种创造欲的表现!”(第123页)“我知道,我也会调整我来适应你,使你常看常新。适应了你也并不是没有了我,却反倒我也活的有滋有味,反过来说,就是我为我活的有滋有味了,你也就常看常新不会厌烦。女人的作用是用来贡献美的,贡献出来,也使你再有强烈的力量去发展你的天才”(第124页)。
这番话,不是一个从小县城来的普通女子能说的出来的,无宁说,它直接说出了庄之蝶或贾平凹本人对女人的看法,从唐婉儿嘴里说出来,至少也是鹦鹉学舌。一般说来,贾平凹笔底下的女人都是没有自己思想的,她们的一点思想只能从男人那儿获取。几千年来中国的女性的确就是这么过来的。而一旦男人的思想奔溃,女人在思想上就越发一泻千里,往往比男人更显得激进(如今天中国的一些“女权主义者”),行动也更加大胆(阴盛阳衰)。清虚庵的尼姑慧明师父便是这种女人的典型的代表。她年纪轻轻便削发为尼,深研佛理,但决不是为了遁入空门,而是为了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向男性世界挑战。她与多名男子发生关系,但却始终能保持一种圣洁和高深的气质。她向牛月清介绍她的经验之谈:“在男人主宰的这个世界上,女人要明白这是男人的世界,又要活得好”,“女人就得不断地调整自己、丰富自己、创造自己、才能取得主动,才能立于不会消失的位置”(第484页),“女人对男人要若即若离,如一条泥鳅,让他抓在手里了,你又滑掉……所以,女人要为自己而活,要活得热情,活得有味,这才是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真正会活的女人!”(第485页)这种中国式的“女权主义”,归根结底是以男子的绝对统治为前提的,哪怕这种统治并不以暴力、而是以“纯情”的方式,以“文化”、“文雅”的方式实行。女人只有以男人为标准才能“创造”自己,这种创造便没有什么创造性;女人“为自己而活”、“对自己好一点”(正如护肤霜的广告词所说的)也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男人,则她们是否真能“取得主动”、成为“真生会活的女人”,也就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男人的兴趣和能力。如果男人兴趣转移、能力有限,女人的一切“创造”和自信自怜便毁于一旦。
所以,当庄之蝶以“文化”的名义将他的女人们的原始生命力激发出来时,由于他实际上并不具备皇帝那样强大的“痞力”来无条件地拥有她们,控制她们,他就只能无可奈何地眼看着他们一个个走向毁灭,并清楚地意识到这整个是一场罪孽、一片地狱的煎熬,他内心一点也“潇洒”不起来。因此尽管这些女子在遭到毁灭时没有一个对他心怀怨恨,反而对他更加顶礼膜拜,但他越来越感到困惑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个坏人吗?”(第418页)这其实也是作家贾平凹的自我发问。要好,想作个好人,为此而不甘屈从于世俗的虚伪;但世俗中充满虚伪,因而他极力要寻求现实中的破缺,以显露真实;然而,这痞性不正是出于纯情、“要好”,经历磨难,几经错过而终于求得的吗?庄之蝶深为后悔:“多年前与景雪荫太纯洁了,自己太卑怯胆小了,如果那时像是现在,今天又会是怎样呢?庄之蝶狠狠打了自己一拳,却又疑惑自己是那时对呢,还是现在对呢?”(第257页)
其实,《红楼梦》中警幻仙子早就说过,那“意淫”(如当年的庄之蝶)和“皮肤滥淫”(如今天的庄之蝶)尽管“意虽有别”,毕竟“淫则一理”。纯情的回到本心,与痞的从本性出发,恰好成了两极相通。当贾宝玉的“红楼梦”破灭后,庄之蝶再也不能把梦幻当现实了。但梦幻又始终纠缠着他,使他以为那里还有一个“真我”,不同于他实际做的:他是堕落了,但他的“真我”完好如初;他淫乱,但他在幻想中贞洁;他痞,但他付出的是真情。他不知自己是谁,是好人还是恶人,但他没有力量、不敢、甚至不愿意摆脱这种双重自我的混沌状态,因为要他弄清这个问题,这等于要他直面丑恶的现实和灵魂的肮脏,放弃一切自欺来忏悔。他宁可自恃纯情而怪罪于他人。例如,“为了摆脱困境,他开始用关于女人的种种道德规范来看唐婉儿,希望自己恨起她,忘却她!可庄之蝶想不出唐婉儿错早哪里,哪里又能使自己反感生厌?”(第487页)他竟然援用他自己首先破坏的传统道德来为自己开脱罪责,怎能不陷入自相矛盾!
要么,他就必须彻底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干一番惊世骇俗的事,哪怕像皇帝那样公然妻妾成群。但他不能彻底,他既无能力,也无胆量。他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实现他作为男人的动物性能,只在幻想中使自己成为一名男子汉。但他的结发妻子正式向他提出离婚后,他就真正崩溃了,他的一切愤世嫉俗和反潮流的故作潇洒都脱落下来,显出他骨子里不过是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一种变态标本。无论他如何激进、如何超前、如何解放,他的根是家庭,这个家庭尽管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生机活力,还日复一日地消磨他男人的自尊自信,几乎使他成了一个不能人道的废人,但他仍然不能离开它。一旦被连根拔起,他就蔫了。庄之蝶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车站候车室里。他到底要到哪里去?为什么出走?这些都没有明确的交代。庄之蝶决不是一名战士,而只是一个逃兵,不仅是逃避社会和现实,而且是逃避自己。他以自己内心的赤诚为据点去寻求社会的“破缺”,可是当他发觉这破缺不在别处,正在他自己内心深处时,他便胆怯了。他可以承受别人的指责和轻蔑,但他无法直面自己的罪孽。他的一切真诚和纯情到头来都成了虚伪,都成了勾引女人满足自己动物性情欲的手段。不论他的出发点是如何要“好”,他都摆脱不了成为“坏人”的宿命,因为人性本恶。
但贾平凹还没有反思到这一层,否则他的灵魂就永远也得不到“安妥”了。灵魂之所以是灵魂,就在于它永远不能在物质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安妥和归宿。真正自由的灵魂是注定的流浪者,只能居住在虚无之乡。它与物质或肉体的区别就在于它是“无中生有”,是凭空创造。庄之蝶的悲剧并不在于他与社会抗争的失败,而在于他的灵魂的软弱无力、打不起精神,无法战胜自己的劣根性。贾平凹的悲剧也不在于绝境中、在中国当代灵魂的毫无希望的生存状态中“安妥”自己的灵魂,而在于他无论如何也还是想要使自己的灵魂在世俗生活中寻得“安妥”这一强烈的愿望本身。这也就是对那曾经一度那么妥帖辉煌、而今早已被废弃的灵都的无限留恋、无限伤怀。只有在这种留恋和伤怀中,他才感到自己内心仍然保留着一股温热的血脉,一种人性的赤诚,一番超越当下不堪的现实之上的形而上的感慨。
二
在《废都》中,我们除了看到男主人公和一个个的女人的暧昧关系之外还看到一种整体的氛围,一种文化气氛,这才是作者真正要渲染、要标榜的东西。说到底,庄之蝶凭什么能够引得一个个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女人如灯蛾扑火般地趋之若鹜?不正是凭这种妙不可言、深不可测的文化涵养吗?与这种文化涵养相比,世俗生活的一切,包括人们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生活享受,都显得那么低级庸俗、虚幻不实。尤其是对那些自我感觉颇好、尚未被自卑心理引入对生活和命运不公的愤懑嫉妒,尚未泯灭对人生理想目标的追求的女子来说,庄之蝶无异于一个实实在在的精神宝藏,在他那里有着一个五彩斑斓的华严境界,显示着生活应有的本相。
然而,庄之蝶的文化涵养之所以显得深厚、玄妙、醇香四溢,并不是由于他的积极进取和创造性的自我陶铸的结果,而恰好是由于他的颓废、伤怀、念旧和返璞归真。这也是整个小说多着力强调的思想倾向。在西京城里,庄之蝶代表文化的最高层次。古今中外一切激动过、诱惑过人类心灵的玩意儿他全部看过了,听过了,领教过了,欣赏过了。但最终,他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真正新鲜的东西。他的目光越来越沉浸到那些远古的、代表人类蒙昧时代的精神家园的东西中去,从中体味人的本真的存在和意境,就像他从那早已失传了的“埙乐”中听到的那样:
……你闭上眼慢慢体会这意境,就会觉得犹如置身于洪荒之中,有一群怨鬼呜咽,有一点磷火在闪;你步入了黑黝黝的古松林中,听见了一颗露珠沿着枝条慢慢滑动,后来欲掉不掉,突然就坠下去碎了。你感到了一种恐惧,一种神秘,又抑不制地涌动出要探个究竟的热情;你越走越远,越走越深,你看到了一疙瘩一疙瘩的瘴气,又看到了阳光透过树枝和瘴气乍长乍短的芒刺,但是,你却怎么也寻不着了返回的路线……”(第111页)
在一个遍地物欲汹汹的年代,庄之蝶这种闭眼沉吟显得那么独出一格、超凡脱俗。他并不是一个迂夫子,相反,他体现了每个世俗凡人在感受到生命痛苦时(如果凡人也有痛苦的话)所自然而然地梦想回复的那种懵然无知的原始状态。寻根就是寻求纯情之痞或蛮痞之真情,它是对现代生活否定人的本性的抗议。然而,正因为人类生活的成长和进步、人的历史和文明进程不能不以这种人类本性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为根本动力,因而这种寻根实际上又是对人类的现实本性(即要长大、要发展)的一种逃避,它注定是感伤的、悲剧性的、软弱无力和没有希望的。它没有承担自己困难的勇气和力量,只徒然呈现了人的心地的纯净和善良:一种极其狭隘、绝望、幼稚和不切实际的纯净和善良。它在被作为自觉的目标刻意追求时往往显得可笑和虚伪,在付诸实行时则又变得可怕和残忍,因为它想用已死的虚幻回忆来强行摧毁虽已患病但毕竟没有死灭的生活本身。
幸好,庄之蝶只是一介文人,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利将他的理想和情感在现实中推行,他惟一能做的只是用一种象征性的举动惊世骇俗地表达他回归自然的理念,即像一只牛犊一样趴在奶牛肚子下直接用嘴吮奶。在《废都》中,那头供给庄之蝶以奶汁、其实毋宁说供给他以精神上的奶汁的奶牛正是庄之蝶良心的象征(同样,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大青马是章永璘的良心的象征。这些作家总喜欢用驯良的牲口来表现人的灵魂)。这奶牛大智若愚,虽然不会说话,却有比人类更加深刻透彻的思想。“牛的反刍是一种思索,这思索又与人的思索不同,它是能时空逆溯的,可以若明若暗地重现很早以前的图象。这种牛与人的差异,使牛知道的事体比人多得多……所以当人常常忘却了过去的事情,等一切都发生了,去翻看那些线装的古书,不免浩叹一句‘历史怎么有惊人的相似’,牛就在心里嘲笑人的可怜了”(第140页)。这牛真是个天生的“后现代主义者”,它坚信“人与所有的动物是平等的”,“人也是野兽的一种”,“可悲的正是人建造了城市,而城市却将他们的种族退化了”(第142页)。于是它操着法兰克福学派和罗马俱乐部的口吻把人类在20世纪所干的一切荒唐事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水源危机、生物链破坏……一一骂了个遍。人类的养尊处优已使人种退化得不如一只兔子,甚至一个七星瓢虫。“牛在这个时候,真恨不得在某一个夜里,闯入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家里,强奸了所有的女人,让人种强起来野起来!”(第254页)奇怪的是,这恰好是当年那些到处寻找“真正的男子汉”的女人们所暗中渴望的。当然,这种男子汉如果不是采取粗暴的兽性而是像庄之蝶那样采取文化的、纯情的方式,将更得女人们的欢心。中国人需要的并不是真正兽性的阳刚之气,而是一种具有阳刚之气的文化。但很可惜,这文化恰好是阴柔的、扼杀阳刚之气的。于是众多的小说家便发挥自己天才的想象力,捏造出了像庄之蝶、章永璘这一类既有高雅的文化情致、又具有令人羡慕的性能力和“野性”的男人形象,其实不过是一种画饼充饥的空想罢了。
因此,庄之蝶的虚假,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缺少这样的实例,也不是贾平凹刻意构想出来的那些情节(如头一次见面一个文化人就可以和一个陌生女人两情相愿地上床)如同天方夜谭,而是根本上的不可能。中国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即越是真诚的文化人越是表现出性无能(其结果是怕老婆“妻管严”),只有那种“两面人”,才能在“文化”的面具底下为人的本能和野性(兽性)留下一席之地;再就是那些缺少文化教养的村夫村妇,他们的野性较少受到残害和压抑,反而有一种轻松自如但痞里痞气的表露和发挥。中国文化人在性心理上的这种心理障碍,不是通过文化上、思想观念上的“回归原始”可以消除的,正相反,当他把这种回归当做是一种高超、纯净的文化来追求、来标榜时,他只是突显了自己已被这个文化本身禁锢的毫无出路的绝望状态,从而加重了自己的心理负担,导致虚火上升而底气不足。这正是当今文人们以各种方式冒充阳刚之气的内心根由,也是许多文人不仅在作品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渴望堕落”、玩味粗野、流于鄙俗的最终根由。我们看对庄之蝶和阿灿做爱的描写,就深感文化人对轰轰烈烈的爱的想象是何等可笑(第303页)。
所以在《废都》中,庄之蝶对现存文化的一切否定和愤激之辞都带给人一种“理念先行”的、无的放矢的印象。人们不明白,对这样一个他在其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的世道,他为什么那么深恶痛绝。我们倒是能够合理想象:这只不过是当今文人的一种姿态,一种愤世嫉俗的时髦,仿佛不如此便显不出文化的高超和思想的先锋似的。庄之蝶把哀乐捧为最上乘的音乐向人家推荐,说“只有这音乐能安妥人心”,就显得有几分做派;唐婉儿说别人不讲究是邋遢,“他不讲究就是潇洒哩”(第32页)!倒是点出了庄之蝶故意邋里邋遢的本意。当今世界真如牛月清的老太太说:“让带面具不带,连妆也不化,人的真面目怎么能让外人看了?”(第40页)其实老太太的担扰是多余的。真诚如庄之蝶,也是有自己的面具的,只是他并不自觉罢了。不带面具就是面具,而且是更隐秘的面具;否定文化也是一种文化:这就是我们民族千年来真正的睿智之所在。庄之蝶并没有表露出真正的内心矛盾和冲突,尽管他满脸一副“苦莫大焉”的模样,作者和许多读者都会不由自主地对他的生活羡慕的要死,觉得他哪怕做了“花下鬼”,也不枉风流潇洒了一世。从作者对庄之蝶的这种欣赏和美化中,我们不难猜到事情背后的真相:这一切手到擒来的风流韵事和要死要活得感情纠葛都是作者胡编出来的,现实中的庄之蝶实际上被周围社会和自己头脑里的传统观念束缚得一动也不敢动,即所谓“有贼心无贼胆”。这才能解释他对这个社会所通行的伦常规范的深仇大恨。人与人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容易沟通的,尤其不容易以“文化”为媒介沟通。读过庄之蝶的书就想和他上床的女人也许不是没有,但那只属于“意淫”的范畴,从那里进到“皮肤滥淫”还有着漫长的路程,而且往往是半途而废。因为这两者潜伏着内在的矛盾,即“意淫”是以对方的贞洁为基础的,一旦实现为性爱,便是对这基础的破坏;理想一旦破灭,便将“文化”降格为“痞”了。当贾平凹自以为是他可以用劳伦斯的审美眼光来看待这种痞,来把性爱上升为一种人类生命最美丽的花朵时,他似乎忘了,查泰来夫人既不是看中梅乐士的名气,也丝毫没想到对方的文才,而仅仅是坦然面对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对一个健康有力的男人的自然需要而已。而这正是我们的文化、也就是庄之蝶身上吸引女人的那种文化所极力鄙视和斩杀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像庄之蝶这样诚实的文化人,身处当今这样的一个四处埋伏着物欲、情欲和阴谋的社会,怎么可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反而像真正的儿童那样动辄敞开自己隐秘的心扉,不但未遭暗算反而屡屡中、逍遥法外呢?怎么可能轻易就获得众多女人死心塌地的真情、获得那么多“以心换心”的挚爱(这种挚爱甚至超越于正常的嫉妒心之上,使庄之蝶被当作人人为之献身的神来崇拜)?作者最后让他悲悲戚戚地死于心脏的不堪负担,正如那头奶牛死于现代文明一样;但其实,使他毁灭的并不是外在的环境,而是灵魂的绝症。
显然,是贾平凹“寻根”的理念制造出了这一切幻觉。他陶醉于中国几千年来文人士大夫梦寐以求的回归理想,而未发觉这一理想一开始就是既不合逻辑也不合生命自身的规律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将来更不存在退回到原始人类如同赤子般互不防范的社会中去的可能。人们历来用远古大同理想为自己的政治主张贴金,不过是利用了大众文化的不成熟、不独立以便理所当然地充当家长罢了。在这方面,文人士大夫千篇一律地成为了这个大众文化的幼稚性和依赖性的代表或代言人。这不仅使他们在权利面前本能地作赤诚状、纯洁状和婴儿状,而且使他们即使在拒斥和远离权力、甚至成为世俗社会的愤激的批判者时,也显得那样幼稚天真,充其量是一个儿童的自暴自弃。如果说,当年屈原的自沉还表明了一种真正儿童式的真纯的话,那么当今文人所标榜的“陆沉”则更多的是一种市侩的狡狯。人们现在已经知道,“不活白不活”,对世俗的反抗居然也可以用来作为自己在世俗生活中谋取平日被自己和社会所压抑着的世俗欲求的诱饵,使这种世俗欲求成了冠冕堂皇的“个性解放”、“思想启蒙”,成了最先锋的济世和救世宣言。似乎当人们在一天早晨醒来,发现一切文化都只不过是鬼话,人们只要赤条条一丝不挂地走上大街展示赤诚,就既可以使自己获得为所欲为的快乐人生,又使社会民风淳朴、不生机心,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庄之蝶只不过是率先身体力行了这一理想而已,属于“先赤起来的”一部分人。
可见,对“废都”的怀念绝不是一种进取的思想,也不是什么启蒙思想(尽管它以西方最激进的文化批判为参照),而是放弃主动思想,听凭自己未经反思的情感欲望和本能来引领自己的思想(跟着感觉走)。从这种意义上说,所谓“安妥破碎的灵魂”云云只不过是对一切思想的解构,使自己的灵魂融化于那充塞于天地间、如怨如诉的世纪末氛围中,以自造的幻影充当自欺欺人的逃路而已。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灵魂的本真痛苦,一切“我好痛苦好痛苦、好孤独好孤独”的自诉都只是在撒娇做派,意在求得他人的呵护和爱抚。当代作家的灵魂何时才能真正振作起来、奋发起来,不是陷入陈旧的语言圈套而走向失语,而是努力为自己创造新的语言呢?
(作者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收录于《灵魂之旅: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存意境》,邓晓芒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