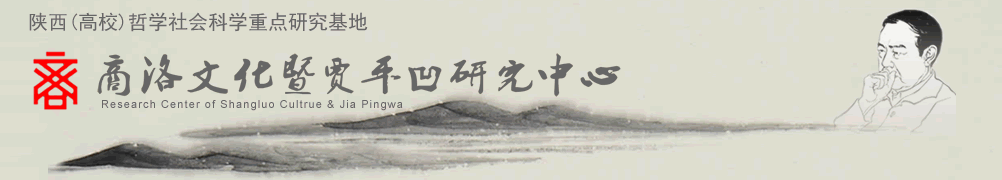李其纲/文
又是一条河,《浮躁》中贾平凹又写了一条河。我们已经习惯瞧见贾平凹笔下淌出一条又一条河。那河从秦岭上蹦趾下来,淌出一片滞重幽远或是平和宁静的优伤和快乐。那是小月横一叶扁舟与门门嬉闹的河(《小月前本》),那是孙二娘一曲清歌为船夫们洗尘祝愿的河(《火纸》),那是流着古老的乞月的各歌声的河(《天狗》)总之,那河是横着洞箫或浅吟或呜咽含蓄蕴藉之河。
此河非彼河,就是说,这河给予我们的审美感受与已往的不一样。这不仅仅在于贾平凹写了这河的喧嚣浩荡、性情暴决,更在于这河在气韵、气势上统摄了全篇的结构、内涵及美感风格。这条河改变了贾平凹。贾平凹说得明白,这是一条“全中国最浮躁不安的河”。倘若说,在这篇洋洋三十余万言的宏篇巨制中有所谓“文眼”的话,在这繁复多变的情节运转结构中有所谓枢纽的话,那么,这条河个性鲜明的特征将毫无疑间充而当之,那就是—浮躁。
浮躁:人文背景下的民族心态的一个侧面我们曾经有过的心态、沉默。当我们抬起脑袋重新打量急速变幻的世界时,世界让我们眩晕新奇和陌生我们企图伸手抓住在我们沉默时匆匆掠过我们面前的那一切,然后我们还企图抓住正在现实地发生的那一切。我们极力把已经变得萎缩、干枯的心灵拓展得宽大些、再宽大些。然而,我们抓着了这些又漏掉了那些,容纳了那些却又挤掉了这些,于是我们焦灼我们不安我们激情难耐我们急躁惶惑。我们拆掉了那河的堤岸—沉默。我们任那河一泻无羁汹涌澎湃挟泥沙翻浊浪。我们成了那河—浮躁。
在这个意义上,浮躁并不是我们修养的一份鉴定,并不是某个个体性格的确认。如果说,浮躁是我们的血之潮汐漫出的精神特征,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凭借于此而走进《浮躁》,凭借于此而认出与我们不无相似的人们。
首先当然是金狗,这个仙游川矮子画匠的儿子,以他强烈的人文精神为我们瞩目。也许他不无张狂,幻想着有月亮那么大的一枚印章,“往那天幕上一按,这天就该属于我了”;也许他不无狡诈,利用田氏家族的势力打败巩氏家族,、然后又利用巩氏家族的势力打败田氏家族;也许他不无迷惘,在利用宗族矛盾救出雷大空后,却感觉到身陷在巨大的权力之网中,这网使他感受到以恶抗恶的“耻辱”;也许他不无脆弱,沉溺于与石华的肉欲关系中而无力自拔……但这并不妨碍金狗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大写的“人”。他的不足与缺陷,他的病态的亢奋与激忿,我们都可以在他企图与之抗衡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找到某种论释。这就是说,当我们承认浮躁的精神特征是相伴着浩劫之后人的解放、主体精神的确立、价值观念的重新发现而不可避免的话,我们同时也就连带着承认了任何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和价值的解放、确立和发现都是相对于对立面的存在物而言,如同我们面对悬崖撑篙行舟,篙弯舟行,在篙子的弯曲中我们同时发觉悬崖的静力。
是的,正是在金狗的这种扭曲中我们发觉了那种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的静力—它异乎寻常地呈现出某种超稳定性。且不说绵延全、四十年之久的巩、田二家的家族之争蔓延至州行政公署和白石寨县委—金狗的许多作为正是斡旋于其中的结果;且不说田一申、蔡大安对田中正的人身依附关系—田中正不止一次地耍尽手腕想把金狗拉入这一关系;且不说田中正强奸小水不成而吐出的狂言:在两岔乡没有他想玩而玩不到的女人—金狗正是在这一场斗争获胜后痛感到一种巨大的“耻辱”……我们仅以金狗报考《州城日报》记者一事为例。记者的名额之所以拨给两岔乡,是因为县委书记田有善想培植自己的家族势力;而当金狗凭借着自己的主体力量、才华和学识考取《州城日报》的记者后,金狗并没有意识到是他自身的努力改变了自身,他依然坚执地相信,倘若没有田中正的首肯,他是不能够走出两岔乡,走向他所向往的州城世界的。这样,他不得不违心地与芙英订婚、不得不违心地割舍对小水的爱,以一种暖昧的暗示迎合了田中正,同时,在与小水告别时,在与石华相处时,又以一种自栽的方式、一种自我沉沦的方式发泄这巨大的屈辱、吞咽这巨大的屈辱。固然,这暴露出金狗精神状态的某种失重、某种心灵的倾斜,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浮躁。但至此,我们至少可以说明,笼罩在《浮躁》中的人文背景,并不仅仅是正向的主体精神的确立,它还意味着这种已经确立和正在被确立的主体精神的逆向:封建性的、呈闭锁状的、盘根错节的人际力量和农业文化力量正强有力地卧在那儿,它的静力与人文精神的前趋力呈抱角之势。在这个意义上,“浮躁”所内蕴的躁动的力量就不仅仅在于它本身的作用力,也在于与它的作用力对峙的反作用力,就是说,“浮躁”内蕴的力量是一种合力,当这种合力外化为某种精神特征时,它就不能不是理智与盲目、纵欲与养性、善与恶、建设性与破坏性、沉溺于直觉与诉诸于理性的统一。它成了我们解开金狗性格全部复杂性的一把锁钥。
不能不想到于连·索黑尔。金狗说: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于连·索黑尔说:我是一个乡巴佬。金狗占有了乡党委书记的侄女芙英后感到十分痛快;于连.索黑尔在占有了市长夫人后感觉到报复的快意。不过,金狗远比于连·索黑尔幸运,于连·索黑尔是在他站在被告席上时,才对他处的阶级、社会环境及自身有切肤的认识,金狗则不然,他在几经挫折后,他的同时代人的经历以及喧嚣不已浩荡不已的州河就给予了他富有时代哲理的启迪:人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和低文明层次的不谐和成了目前的普遍的浮躁情绪的特点。这构成了金狗对于时代和社会的一种领悟,同时也构成了金狗对于自身的一种把握,不管这种领悟和把握如何拘囿于精神的范畴来解释精神现象,它毕竟已经能摸到了当代中国特定的人文背景下独有的民族心态,而一旦展开这一命题,金狗与金狗们将或迟或早地认识到对于精神障碍的克服、对于浮躁之气的涤除并不仅仅是个纯粹精神领域的命题,在根本上,这一命题是物化的,恰如马库塞所言:人类劳动的彻底物化将切断把个人缚在机器上(包括土地上—加重点号部分系笔者所加)的锁链—即他自己的劳动用来奴役他本身的装置—从而粉碎这种物化了的形式。①亦恰如《浮躁》的结尾金狗在州河上操起了小火轮的举措所暗示:正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总体上制约着人们的精神选择和精神构成。斯丹达说:在法国有二十万于连·索黑尔②。那么,在今日之中国呢。有多少金狗聚合成一个焦点从而凸现出民族心态的一个侧面呢?二十万?二百万?抑或二千万?
浮躁:原欲与超越
如果把“浮躁”看作当代中国特定的精神现象,并且这一特定精神现象又有着它特定内涵的话,那么,这一精神现象的内核又是什么呢?《浮躁》为我们提供了寻求这一答案的艺术契机。我们不难发现,在《浮躁》中有着颇为相似的“浮躁”特征的有两人:金狗和雷大空。尽管他们的个性特征千差万别,尽管他们的文化素养相当悬殊,但在不满意自身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环境、力图跳出土地的束缚这一点上,两人却殊途同归,共同走向了州城。当他们在州城喧嚣嘈杂的市声中彼此相握,频频顾盼五光十色的城市景观时,他们压捺不住最初进入城市的欣喜,感官处于高度亢奋状态中,一种浮躁的情绪和特征随之出现:金狗沉溺于与石华的欲海之中,雷大空的口袋无意中竟掉出许多用处和对象皆不明的避孕套。心灵在城市的挤压下急逮倾斜,但在这倾斜中却颠出了我们企图捕捉的东西:正是人的朴素的、本能的生命冲动和物质欲望,而不是某种空洞的政治术语勾勒出金狗和雷大空精神一隅的风貌,构成我们称之为“浮躁”的精神特征内核。换句话说,“浮躁”这一精神现象如同其它精神现象一样,都不是纯粹精神的派生物。它与人的原欲有一种塔和塔基一般相互依存的联系;它以自身的复杂性肯定了如下的表述:并不存在任何超脱肉体的精神力量,而那种自以为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象中才具有精神力量。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原欲等同于道德尺度中的恶,因为人的原欲、人的生命冲动在精神化的过程中,既可能产生道德尺度中的恶,也可能上升为人改造自然、创造人所要求的物质生存环境和方式的力量,上升为道德尺度中的大善大美,即它有可能被导向各不相同的极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否定人的原欲对人自身具有永恒的诱惑,这就如同只要有城市只要有农民,城市对于农民永远是一种诱惑一样。
是的,永恒的诱惑。贾平凹已经不止一次地写到这种诱惑。《古堡》中的老二觉得只要能接着城里女子睡上一宿“死了也值”,最后以自己鲜活的生命殉了这痴情。在《浮躁》中,贾平凹更是在城乡交织的经纬中,写出了三种各不相同的农民进入城市的三种方式。其一,巩宝山方式,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坐上州府大堂”;其二,金狗方式,凭学识凭才华,考取记者或考取大学;其三,雷大空方式,经商,发财,以金钱作矛以智慧作盾。耐人寻味的是,这三种方式都潜藏着某种相似的危机:取第一种方式的巩宝山,悄悄地由人民的公仆而转变为人民的“主子”,手中的权力也通过儿子之手进入了商品流通的渠道,而早年的结发妻子则被他象扔掉一件用旧了的物品一样扔掉了;取第二种方式的金狗和某个山里娃子,也都因为某个城里女子经历了一场难以自拔的情感危机。不同的是,金狗终于因为“菩萨”小水的佑护而脱身,而山里娃子则在扼死了爱着他的教授女儿后与其同归于尽;取第三种方式的雷大空,财大气粗之后,以一种阿Q式的心理处处与县委书记比气派,比开会的时妹谁迟到得更多,比谁更能够挥金如土,经商则买空卖空,导致银挡入狱,最终被人陷害,死于非命。
然而,就没有第四种第五种第六种第n种方式吗?
倘若说浮躁的精神内核是人的原欲的话,人就不可能超越和驾驭人自身的这种欲望吗?对于千百年来在黄土地里抠食的农民来说,他们在心里羡慕遥遥眺望的城市难道永远是恶的渊蔽吗?
显然不。人并不是纯粹的欲的存在,就如同人不是纯粹的精神存在一样。人同时还是社会的存在、文化的存在和历史的存在。人的这一系列存在的结果表明,人不可能不受到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制约和影响,并且,正是这种制约和影响使得人的原欲有可能上升为生气灌注的理性力量,有可能成为刺激生产力发展的酵母,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对人的欲的诱惑同样可以得到升华并被超越。就《浮躁》而言,它已经传递出这方面的信意。小水所梦的“民主选举县长”难道不是一种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方式吗?何况,即使旧有的方式,也不在于方式本身,而在于驾驭这种方式的人的精神素质,“金狗银狮梅花鹿”所驾驭的小火轮难道不是对旧有方式新的使用吗?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经商,就是与雷大空的方式相同,但目的和本质迥然相异的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空,同样激荡着心灵的呐喊,同样映现出灵魂的躁动,如果说这也算一种“浮躁”的话,那么,它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它是源于自我、通过社会的中介并滋润社会、同时又被社会改变了的自我映象,如同血通过心脏并滋润心脏并被心脏改变后又回复到血管。
金狗在欲的原始躁动下走进州城,而后在州城单枪匹马、处处忍受精神和肉体的双层苦闷,最后又回到生他养他的州河上—他走过的是一条超越原欲、超越自我的道路,尽管他似乎绕了一个圆,但这个圆却是上升的螺旋。在他变得坚忍沉着的气质中,在他摒弃空谈玄思崇尚务实的作风中,凭着他对中国农民和城市的深刻体察和理解,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还会再度走进州城,那时他不再是孤独的。但不论未来怎样,现实的金狗走过的这个圆已经烙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历史是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既不是纯粹的、净化的,又无法被省略。它有那么点残酷。
浮躁:历史进程的价值尺度
这是另一群人们。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们褐黄色的肤色如同褐黄色的土地;他们古老他们沉默他们滞重犹如枯水季节的州河。他们是泥捏的一群男人。他们洛守祖宗的遗训,对背弃土地的金狗斥之为“男双旋,拆墙卖砖”,骨子里他们是重农主义;他们信奉传统的人伦,对田中正与嫂的通奸嗤之以鼻,一旦“熟亲”则无可非议;他们崇尚薄利厚义的古风,对进了城的金狗抛下小水报之以极大的义愤,福远说:死了我也不会做这等绝情的事;他们既膜拜权力又痛恨权力,他们既眷恋家园又厌恶家园,他们既信命又反抗着命·,·…福远死了,为了县委招待所的餐桌上能多上一盆熊掌,他把自己的血肉之躯置于熊掌的蹂嗬之下;矮子画匠活着,但田中正响一个屁他当作一声雷;七老汉活着,每一次撑排过滩他都念念不忘为供奉于匣中的小白蛇燃上一柱香;秦文举活着,撑一叶渡船喝酒、调笑女人、发发田中正的牢骚,除此之外,他该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呢?
还有一群人们。
她们是水做的骨肉。她们坟好她们善良,她们都处在花骨朵般让人怜爱的年龄。也许只是一种偶然,熟悉贾平凹创作的差不多都不难发觉,只要是处于这一年龄当口的女子们,贾平凹在笔卞是不愿太伤害于她们的。《浮躁》亦如是。菩萨般的小水自不消说,就连“可人的小兽”芙英,在金狗落难之时也满掬辛酸之泪,全然忘记了金狗报答她热炭般灼热的感情的是一块坚冰;而金狗既厌恶又难以割舍的石华,更在金狗身陷图圈时伸出救援之手,不惜吞咽下女人最难以吞咽的耻辱,服了安眠药让一个呆傻的公子哥儿玩弄了一通。她们是水,但她们和在泥之中,这就是说,她们得承受双重的苦难。不静岗的寺庙里,行将老去的老婆婆在唱着女人们的一生。她们唱啊唱呀,从开天辟地女蜗捏人开始,唱到“人怎么生人,生时怎么血水长流、胞液腥臭,生下怎么从一岁到两岁、到三岁……到长大了怎么去冬种麦夏播秋,怎么狼来要吃肉,生虱来吸血,怎么病痛折磨,烦愁熬煎,再到婚嫁,再到性交、怀孕,再到分娩,一直到儿女长大了又怎么耳聋眼花,,受晚辈的歧视,最后是打打闹闹争争斗斗几十年了蹬腿咽气……”毫无疑间,女性不仅在生理上更得在心理上承受比男人们重得多的负荷,在封建性的、以小生产方式为特征的农业文化中,她们处在最底层。《浮躁》以小水的两次婚变,最终方与金狗结合的曲折感情历程,具象化地展示了这一点。就文化心理来说,小水是传统的,忍让、克己、认命、中庸、谦和,这无论从她遵从媒约之言嫁给“小女婿”,还是她对金狗与芙英的婚事所持的宽容态度中均可显现出来。
他们和她们—都是不愿跪着但又在无意识(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中双膝磕地的一群人们。
他们和她们都与“浮躁”无缘。
他们的心理结构是稳固的,从代代相传的歌谣古训中,从相沿成习的乡俗民风中,他们建立起自己的行动准则、伦理规范;他们并不孤独也无所谓孤独,他们自信仍然拥有广裹的空间和众多的人口;他们也许不无麻木不无迟钝不无愚味,但对任何异己的新的事物却抱有让人诧异的敏感……如果说“浮躁”的精神实质是面对一个日益开放的世界持一种开放的姿态,表现出巨大的受容力的话,那么他们稳固而滞重的心理结构和心理内涵则刚好相反,以一种封闭的姿态保存自身,表现出巨大的排他力量,即使他们的敏感也表现为排他的需要。但是正是他们的呈静态的稳固提供了一种参照,反衬出“浮躁”的精神内涵所具有的动态价值:变革因子的活力与跃动,如同静态的原野反衬出高速行驶的列车。在这个意义上,一“浮躁”本身的价值内涵构成了这片土地上变革的历史进程的价值尺度。换句话说,“浮躁”成为一种标志,在死水凝结的地方无所谓“浮躁”;在弥漫着“浮躁”的地方,那地方必然已崛起、生长出新的观念和这种观念赖为倚托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而在“浮躁”与其对立面的存在两者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相互纠缠相互格斗的地方,则必然错综复杂地呈现出一幕幕让人惊心动魄的悲剧和喜剧。
也许还应该着重提一下她们。在这一幕幕悲剧和喜剧中,她们并非是某个客串的角色,她们是正儿八经的主角。倘若最深的古井能够掀起波澜,能够透出几缕“浮躁”之气的话,那么,历史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标识被解释了。令人欣喜的是,她们中已有人用她们操惯了的剪刀剪开了天
幕的一角:大千世界同样开始让她们陌生、新奇、焦灼。在这样的时候,小水开始做两岔乡以外的世界的梦。那个梦是“通过民主选举,金狗当县长了”。
悬挂在文学长廊上的《浮躁》
1827年,斯丹达在《法院公报》上看到了一个名叫贝尔德的青年家庭教师开枪射击自己女主人的情杀案件的详细报导,不久,他就在这个素材的基础上加工改编,构成了小说《红与黑》的基本情节。③
1986年,贾平凹以1985—1986年在陕西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的几个经济案件作为基本事件构成《浮躁》的情节框架。④
这并非奢侈的多余的或无的放矢的比较。当然,这种比较并不忽略斯丹达与贾平凹所处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文化渊源,这就如同我们并不忽略于连.索黑尔与金狗的巨大差异一样。这种比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在强调文学的即时性时,蓬勃的、此时此刻的社会生活并不缺乏它的文学魅力,而且这种魅力并不是瞬间即逝的。
如果说,《浮躁》取材方式与《红与黑》取材方式的相似显示了贾平凹与斯丹达一样的、对于即时的社会生活热切关注的文学家的真诚的话,那么,“浮躁”—这一时代典型情绪的概括,则显示了贾平凹对于当代文学的关注和对于自身创作局限的不断突破。
集中体现了“浮躁”精神特征的金狗,在《浮躁》中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一形象在贾平凹的腹中有一个酝酿、发生、发展、日臻成熟的过程。在《小月前本》中的门门、《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腊月.正月》中的王才、《古堡》中的老大……这一系列人物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金狗的雏形。他们是不安份的,他们对土地不再景仰,对祖宗的遗训抱有漫不经心的轻蔑,他们对自给自足自封闭的生产方式施以撞墙式的突破和冲击:门门搞转手倒卖,王才办起了食品加工厂,老大执著于村外的矿井和矿石。他们也痛苦,村里的老的少的几乎都不理解他们,理解他们的唯有他们心爱的女人。他们是高尚的,感情上是净化的,道德上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孤独宛如为人类盗来冬火的普鲁米修士。然而,在这同时,他们的性格是不是也显现出某种单一和单调呢?在总体上,这是不是也构成了贾平凹创作中的一种人物模式呢?模式总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艺术生产毕竟不等同于合成树脂玻璃器皿可以成批量生产,因而金狗形象的塑造,他的丰满和复杂,在突破模式上的意义上,是可以让我们也让贾平凹欣慰的。
我们已经指出,“浮躁”是一种概括,它概括出我们所处的时代骚动而又充满生气的精神特征:面对历史、现实和未来,我们正在分崩离析的旧价值观念基础上重新建构我们的世界。这是一个扬弃的过程。然而,仅仅是《浮躁》才对“浮躁”这一时代情绪的精神特征给予概括给予一种艺术语言的描绘吗?
显然不。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的孟野们,刘心武《五一九长镜头》中的滑志明,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孟加拉虎”,张承志《Graffiti一胡涂乱抹》中的“他”,……他们或多或少或浓或淡都泄露出压抑在心际缠绕在心际的那种骚乱那种烦躁那种不能自已以命相搏以求一快的情绪。这种情绪的质与金狗的“浮躁”并不是截然相异的,它们共同孕育于同一母体同一水土同一文化背景中。但是,将“浮躁”这典型的时代情绪置于当代中国特定的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中予以考察的,贾平凹是第一人。
①转引自《伊甸园之门》71页。
②转引自柳鸣九主编《法国文学史》417页。
③同上,405页。
④见《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
(本文作者为《萌芽》杂志社副主编,原文刊载于1988年第2期《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