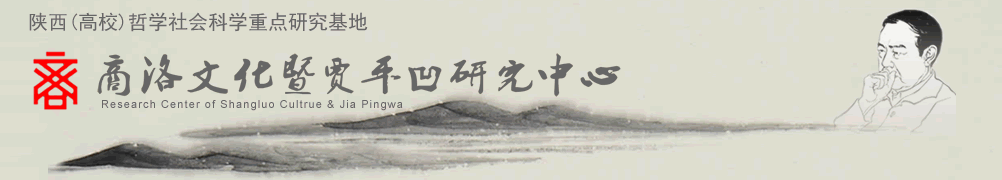程华/文
在文艺创作界,贾平凹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作家。与时俱进,源于作者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并以积极的写作姿态,参与到社会时代的变革之中。八十年代的《浮躁》,九十年代的《废都》,2005年的《秦腔》,贾平凹以他的如椽之笔,深入时代社会的肌理之中,写出现实社会的血肉和精神文化的灵魂。新近出版的《高兴》,是继《秦腔》之后继续关注当下农民工生存境遇的小说。农民工作为特定时代下的社会群体,作者在展示他们整体生存现状的同时,将笔触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挖掘他们内在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根源。与同时代的其他农民工题材相比,贾平凹没有从农民和城市对立的各种外在的社会事件出发展开文学想象,而是着眼于农民工进城打工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追根溯源,用文学参与社会,探索农民工的人生命运和精神旨归;通过底层视角传达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从文明、人性的高度统摄正在发生着的乡下人进城现象,使得文学超越对社会现象、历史进程的直观概括达到人性批判的高度。
一、问题意识与文化反思
2005年春季出版的《秦腔》中有一个细节,作者写到清风镇的老支书秦天义因开掘荒山而被土掩埋,人们在其下葬时竟找不到抬棺材的青壮小伙,偌大的清风镇只剩下妇孺老弱, 清风镇的小伙都到那里去了?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就有了《高兴》最初的写作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城市转移,象征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城市文化形态成为主流。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大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成为新时代的“离土农民”。“‘离乡离土’到了21世纪已成为不可遏制的人潮,并呈现出许多新的社会和思想特征,‘农民工’,‘打工者’已成为新的农民群体的生成”。[1]6“离土农民”是特定时代下的新的社会群体,也是特有的社会问题。用文学形式关注社会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气候并产生一定影响的,多发生在社会改革或社会转型期。上世纪之初的五四时期和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就涌现出一批可贵的“问题小说”,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表达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责任意识。用文学参与社会问题,强调文学创作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和敏锐的洞察力,并通过文学想象达到对社会问题的记录,反思和批判。问题意识,是文学作者可贵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一个具体表现,也是其作品永葆鲜活的法宝。
当下社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扩大,各种社会问题纷纷凸现,农民工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以后,给城市带来农耕文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的信息,他们影响着城市;相反,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以其强大的辐射能量不断改变着他们的思维习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会成为最有冲突性的文学艺术表现内容”[1]8。贾平凹新作《高兴》就是通过文学参与社会的方式,关注这样一群离土农民的现实生存问题。物质生活环境被城市隔绝,是广大农民工普遍的城市生存境遇,贾平凹首先通过对这些农民工生存环境的再现,来表现底层打工者的生存境遇。“池头村”是收破烂聚集的地方,肮脏不起眼的城乡结合部,这里主要生活着由农村来到城里的最底层打工者,他们“既没技术,又无资金,又没城里人承携”[2]438, 只能像“祥子”一样在城市寻找类似土地一样稳定可靠的生产资料,从事最底层的职业,做着城里人“视而不见,见而不理”438[2]的收破烂工作,《高兴》中的主人公大都生活贫穷,挣钱是他们城市生活的目的。五福挣钱养活妻儿老小,杏胡挣钱为还债,刘高兴挣钱为娶妻。垃圾是他们基本的生产资料,但即使这样,他们的生存也是不保障的,遇上下雨天,遇上车祸,更多的是遭到歧视,被城里人隔绝。作者透过这样一个收破烂群体的基本生活状况,提供了这样一幅社会图景,在中国现代化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但却成为城市的“异乡人”。
文学写作者的问题意识不仅在于发现问题的症候,更重要的在于追根溯源。《高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将笔触更多的深入到人物的内心,通过对他们生活态度、性格特征、文化心理的描写,表现这样一个社会群体,都有与城市文化不同的乡村文化的因袭,从揭示他们性格文化根源的角度进而揭示他们城市生活物质贫困、精神贫穷的深层原因。
五福,是刘高兴从农村带到城市的搭档,他就像乡间的一根草,一个“蚂蚁”,其生命原本是属于土地的。五福憨厚老实有力气,他这颗乡间的蚂蚁来到城市的水泥地上,虽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但其基本的生活态度和性格特征并未改变。他的生活态度是具体而现实的,来城市的目的就是生存和挣钱。文章中有一细节描写刘高兴问五福老婆重要还是钱重要,五福不假思索的选择了人民币,这就是农民的实用理性。食色,性也,但食比色更重要,钱比娘们更亲。五福最后在为挣更多的钱的梦想中命丧黄泉。五福在城市丢了命,可五福的尸体还要回到清风镇上入土为安。五福生前不止一次戏谑自己死后,其魂魄要回到清风镇。而当残酷的事实终于发生,也就有了五福悲剧性的返乡情节,这说明中国传统乡民最本真的生死观念。《老子》讲,“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故重死而不远徙”。农民是土命,土地是乡民安妥灵魂的依托和他们生命轮回的根基。农民死时,往往要在土里挖一角掩埋,人与土就有了一种依存感和亲属感。民对土的感情,类似于亲缘和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表现的是主人公对土地的深深眷恋,更重要的是对乡风民俗的精神皈依。五福的尸体最后仍在城市火化,其灵魂飘荡在城市的上空,找不到归依,这是五福的悲剧,其实也是作者的思考:这些在时代转型期,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底层打工者,他们一旦失去了与土地的依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不但生活变得漂泊不定,他们的灵魂和命运也无所依附。作者对五福悲剧命运的描写,实质就是作者对新时期农村底层从业人员命运的担忧和他们生活前景的忧虑,包含着作者深深的忧患意识。
杏胡是池头村与刘高兴合租一楼的另一个拾破烂者,在众多以拾破烂为生的人群中,杏胡是女性的代表。女性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基本上都具有文化的符号性和象征性。在《秦腔》和《高老庄》中,西夏和白雪的形象象征着一种理想的文化态度。有些女性,是与性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杏胡就具有这样两面性。作者一方面展示杏胡泼辣的性格和坎坷的命运,旨在说明在生存竞争愈加艰难的现代社会,女性可能要承受比男性更多的忍耐和艰辛;另一方面,杏胡和丈夫种猪的关系,又使人联想起两性关系。从性文化的角度而言,在杏胡身上,更多的带有民间性文化粗陋的一面,杏胡与种猪的半夜叫床,杏胡与黄八的性戏谑和粗话,无一不展示了具有乡村民间性文化的猥亵趣味。食色,性也,在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生存欲望的同时,对性的渴求也是一种基本的生理需要,在描写底层打工者的城市生活中,作者并未避讳这一点,塑造了杏胡这样一个形象,并通过这一形象来体现底层民众去伪存真的两性文化观念。池头村的夜晚对于这些远离妻儿的乡民来说,是难熬的。在刘高兴、五福、黄八等的聚居生活中,是杏胡带给了这些男人对性的憧憬和渴盼。性戏谑、性粗话是苦重活计后仅有的消遣。他们与时尚的黄段子是不同的。黄段子中包含着对女性尊严的歧视和从黄段子中获得想象性快感的虚伪,而在杏胡与种猪真实的性生活中包含着作者对下苦人的理解和同情。性,在这里,除了用于种根留后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生活。气味辛辣而又粗鄙的性话语形式是在严酷的生存条件下农民在非人状态中最人性的一种表达。贾平凹对杏胡的塑造,并不是为取悦读者,更多的是对农民打工生活状态的完整书写,是对他们情感和生理欲望的真实表现。
在《高兴》中,贾平凹将写作触角深入而细致地探入到这些底层打工者的生活世界和他们的灵魂世界,既还原了他们贫穷、卑微、被隔绝的城市生活,又深入到这些打工者的内心,表现他们的生活态度、伦理情感,写出了他们离乡未离根的乡村文化价值观念和性格成因。他们的劳动态度、性格特征、生死观念、甚至性文化无一不深深的打上乡村文化价值观念的烙印。乡村文化价值观念和现实的城市生活远远不能融合。他们离开土地到城市求得生存,但他们又不具备城市文化所需要的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所以他们只能被“抛”入城市中,如浮萍般飘摇。 “城市文明作为一种诱惑,一种目标,时时吸引着大批乡村追随者,而乡村追随者为使自己融入城市,必须要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思想蜕变过程”[3],这种脱胎换骨的最大阻力,就是与农民工的性格特征、生活态度甚至行为方式融为一体的乡土文化价值观念。乡村文化观念与城市文明的“文化落差与反差”[4]180是导致农民工城市生存困境的最大阻力。作为底层打工的农民群体,如何更好的适应城市生活,如何成为城市文化的有益组成部分,如何在不断改变和适应城市物质生活的同时改变自身的精神世界以适应城市的文化生活。这是作者对新时代离土农民真实生存境遇、性格成因和文化心理及人生命运的思考,这种思考,就不仅仅只是在作品中提出农民工这一社会问题,而是从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内涵揭示出他们生存处境的根本原因。与同时代的关注当下农民工问题的“问题小说”相比,表现出相当深厚的文化内涵。《高兴》延续了作者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等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文化寻根和精神探索,既关注底层农民的生存价值和现实人生,又深刻挖掘他们内在性格的文化成因,既而对他们的未来寄予深深的忧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在关注生民的命运中见证作者朴实而深厚的平民情怀和入世精神。
二、底层视角与知识分子立场
底层视角,主要指叙述者的叙述话语来自真正的底层生活,并以底层人的视野关注正在经历着的底层人生。“所有底层叙述都是作为一种话语实践而存在,它们或者是权威话语实践的产物,或者是知识精英话语实践的产物”[5]。《高兴》创造刘高兴第一人称限制叙述视角,刘高兴是底层生活的经历者,他所操持的是来自底层的“元话语”[5]。从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位置关系而言,刘高兴既是底层生活的叙述者,又是底层生活的见证者,作为叙述者的刘高兴与被叙述的底层生活世界就不是居高的俯视或旁观的赏玩,而是真实的底层生活在演示。从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态度关系而言,刘高兴具有的双重角色和身份,自身所具有的底层生活经验,使叙述者的灵魂能够更贴近底层人的内心世界,感受弱小群体所受到的歧视和伤害。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刘高兴的底层视角,避开广阔纷纭的各类政治、经济事件的干扰,以刘高兴为中心,联络起与刘高兴有关的各色人等和各种事件,限制了叙述空间,但同时延展了叙事的信息含量。使作品便于表现更开阔的生活世界和更本真的生活细节。
刘高兴作为底层叙述者,主要承担着“传达”和“讲述”[6]25的功能。他传达底层生活的信息,讲述底层生活的故事。作者创造这样一个贴近底层的人物来讲述底层的各态人生,“正像生活在场一样,生活以其存在在表演”[7]29,从而展现出开阔的农民工城市生存图景。
忠厚、肯劳作的五福,从不怜惜自己的体力,就象土地上的“蚂蚁”一样,默默耕耘,只为求生存,却也在城市中丢了命,面对五福的尸体,其妻在意的不是五福生命的消失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而是五福可怜的劳动所得;与五福同居“剩楼”的黄八,因常年在外打工,其在家的妻子却被人拐跑,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没有寄托,用挣得的钱寻求肉体的安慰和欲望的发泄,变成了动物一样的城市里的游魂;杏胡和种猪的生活经历更为苦难,留守在家的老母亲和一对儿女,因为一场意外,老母亲竟被火活活烧死,而他们的城市生活最后因法网无情而锒铛入狱。刘高兴视角之下的五福、杏胡、黄八和种猪,他们有生存的欲望,肯吃苦,也想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但无一例外,除了生活环境和物质生活被隔绝外,他们的人生命运和人生处境都很悲惨。他们表现着底层人物生存的辛酸与生命的苦难,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个体生命所具有的普遍性的脆弱、无助、彷徨与无奈。他们是一群城市里被动生存的小人物,他们的命运如同“苞谷杆一样脆弱而飘摇”。文章中有一段主人公刘高兴的心理描写:
“土堆里可能混杂了苞谷粒的,这不足为怪,它是一有了水就生根发芽的,可苞谷粒那里知道这堆土不久就要被铲除运走,那里知道这次生长不可能开花结果,恐怕长不到半尺高就会死亡呢?
多么想活的苞谷苗儿!苞谷苗又是多么贱的命呀
我还能想些什么呢?似乎我想到了许许多多事。”[2]179
在主人公刘高兴的心理世界背后,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作者对农民工城市生活境遇和人生命运的隐喻。这些底层人物在城市文明巨大机器的运转下,他们的存在是渺小而被动的,随时都会被残酷的生活所吞噬。
孟夷纯,是城市生存的另类女性形象,她们在城市生存和挣钱,但却不像杏胡们靠出卖劳力为生,而是凭借女色,出卖肉体。孟夷纯作为发廊女,自觉意识到她与城里老板韦达原本就不是生活在同一精神空间之中,也非常清醒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性出卖的利益关系而与真情无关,但孟夷纯出狱后还是寻找韦达。这是一种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精神沦落。这种灵魂的自我毁灭或沦落,不是刘高兴的爱情力量能够拯救的,也不是孟夷纯自己能够自救的,这是渺小的个体在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压力之下的灵魂迷失和精神的麻木。与孟夷纯的灵魂麻木不同,石热闹在刘高兴的视觉之下,是一个城市的乞讨者。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因先天的好吃懒做,自觉丧失了劳动能力,另一方面,又沾染了某些城市人油滑腔调的劣习,这是新时代下的“张瑞丰”[8]们。孟夷纯和石热闹,是作者关注城市生存的另一类人。他们的悲剧不同于五福们,孟夷纯的生命是寄生的,石热闹的生命变成了躯壳,他们都成为城市里的“死魂灵”,人在物质生存状态中选择文明的同时也迷失了灵魂,作者重要的不是再现他们的悲惨生存处境,而是表现他们的灵魂的空虚和精神的异化。
与石热闹不同,刘高兴的灵魂是充实的;与五福用力气谋生不同,刘高兴是用脑子生活的。他是五福的“军师”,是“剩楼”的“支书”,有与其他城市打工者不一般的精神境界。如果说五福们想获得在城市生存的“物质通行证”,那么刘高兴想获得在城市生存的“精神绿卡”,作为底层打工者,刘高兴除了满足物质生存而外,还需要城市边缘人最起码的精神权利。这主要体现在刘高兴的爱情追求上,“尖头高跟鞋”[2]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形象,它一方面表明刘高兴所心仪的爱情对象不是一般的农村妇女,另一方面,表明刘高兴有不同于一般城市打工者的精神追求。孟夷纯的出现,刘高兴找到了他的爱情。孟夷纯是一个妓女,刘高兴真心的同情并尽自己所能帮助他,刘高兴与孟夷纯的交往与孟夷纯的其他男人不同,显示出对爱情的一腔真心,而且还让我们看到了刘高兴非同寻常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个虽在最底层生活,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却有“在最肮脏的地方高兴得活着”[2]的乐观心态。这是一种在常态人生中抵抗苦难,却有着乐观坚定的生活态度和生活品德,是底层生活中所蕴含着的人性之光。刘高兴的存在,使作者获得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精神想象,是作者对底层城市打工者塑造完美品格,建构理想精神世界的一种期望。
作为叙述者的刘高兴如果仅以底层身份去感受、观照底层生活,很容易滑向农民立场,将农民工的底层生活和城市文明对立起来,“作者若以农民立场考察底层生活,其认识上的局限必然遗留在文本之中,影响小说叙事的深度和美学成就”[9]92。 但从叙述学的方法而言,叙述者常常是真实作者在小说中的“新闻代言人”[10]172。“小说家借作家与叙述者的间离来造成另一个潜在的审视角度”[11]54,叙述者身上常常有作者理性审视城市生活的意识融入其中。
《高兴》中的叙事者刘高兴,同时又具有“隐含作者”[10]173的身份,在刘高兴的叙述过程中,处处隐含着作者的意识。在刘高兴的视角下,有五福、杏胡们的生存悲剧,孟夷纯和石热闹们的灵魂悲剧,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刘高兴们在苦难中的坚强姿态和精神品格。透过这样的生存图景的群体展示,我们不仅看到了转型期中国农民城市生活的全貌,更重要的我们也感受到作者对底层生存状态、人生命运及底层人精神状态的总体评价。而这后一方面,正是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随着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确实取得了进步。但同时也使大量的农村人口丧失土地,大量迁移到城市。在以经济效益论成败的现代化背景下,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的价值立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刘高兴的叙述视角,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不是从历史文明的角度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历史主义的评价,而更多的是从伦理人性的角度,通过关注底层打工者的生存境遇和人生命运,对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现实进行精神探寻和道德的批判。“在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对撞中,我们不能掩盖现代文明给人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戕害”[4]183,“农耕文明在摆脱物质贫困的同时,不得不吸附在城市文明这一庞大的工业机器上走向历史发展的未来;而正是城市文明的这种优势又迫使农耕文明屈从于它的精神统摄,将一切带有丑与恶的伦理强加给人们”[4]185,在《高兴》中,作者正是透过五福、杏胡们的被动而脆弱的生存,孟夷纯和石热闹们的精神迷失和灵魂异化,说明文明的进程对底层人性的戕害。正是在对城市底层苦难人性的描述中,用人性的尺度,来衡量文明社会的进程,进而达到社会批判得目的。
作者在道德批判的同时,更多的运用知识分子的理性审视底层生活,探寻理想的精神世界。在商业文明的冲击下,《秦腔》表现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对即将逝去的农耕文明美德的深深眷恋,而在《高兴》中,作者正视现实文明下底层人民生存的现实,在揭示底层生存悲剧性的同时,借助主人公刘高兴的精神世界,表达出一种社会精神文化的深广意蕴:在底层生活,或者说在生存困境中张扬理智、高兴的生活态度是我们这个时代强调个性价值的人所需要的。在追求个性价值的同时,随时都有困难、竞争和挫折,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如何自由的张扬个体的精神意志。高兴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文化符号。如果说,“浮躁”是80年代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废都”是90年代文化没落者的精神映像,那么,“高兴”就是当今时代人们普遍追求个体生存价值的一种精神想象。
注释:
[1]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失范[J].文艺研究,2005(8)
[2] 贾平凹.高兴.后记[M].北京:中国作家出版社,2007,9.
[3] 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J].文艺争鸣,2005(3)
[4] 丁帆.文明冲突下的寻找与逃逸[J].江海学刊,2005(6).
[5] 李遇春.新时期湖北作家的底层叙述与底层意识[J].小说评论,2007(4)
[6] 赵毅衡.苦恼的叙事者[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7] 法国,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8] 老舍.四世同堂[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79.
[9] 刘云.艰难的历程[J].北京:现当代文学研究,2007(3)上旬刊.
[10] 王成军.纪实与记虚—中西叙事文学研究[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1]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8.
(作者为商洛学院语言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