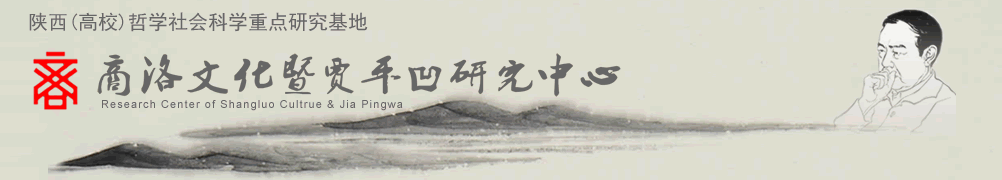席忍学/文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更是如此。每个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因其对西方文学理解的不同而显示出差异。贾平凹从创作出发,对西方文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其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贾平凹认为西方文学具有大境界。“那些现代派大家(指西方现代派大家,笔者注)的作品,除了各自的民族文化不同、思维角度不同外,更重要的是那些大家的作品是蕴有大的境界和力度,有着对人生的丰富体验和很深的哲学美学内涵。”[1](P418) “就是马尔克斯和那个川端先生,他们成功,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趋向而浪花飞扬,河床却坚实的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2](P18)在贾平凹看来,西方那些大作家之所以成功,首先在于他们的作品具有大境界。
贾平凹所说的大境界是什么呢?所谓大境界,就是要表现人类相通的东西,
就是要有人类意识。他说:“要做一个好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就是表达出自
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份态度,这态度不仅是自己的,也表达了更多的人乃至人类的东西。”[2](P17)而且,贾平凹把表现人类意识看作是一个好作家的重要标志。
大境界就是指文学要表现博大的生命意识。“通往人类贯通的一种思考一种意识的境界,法门万千,我们在我们某一个法门口,世界于我们是平和而博大,万事万物皆那么和谐而又充溢着生命活力,我们就会灭绝所谓的绝对,等待思考的只是参照,只是尽力完满生命的需要。生命完满得愈好,通往大境界的法门之程愈短,如果是天才,有夙愿,必会修成正果,这就是大作家的产生。”[2](P17)他认为大作家就是有大境界的作家,大作家的重要标志就是有博大的生命意识,就是要表现博大的生命意识。
大境界指文学应该有大的气度,作品应该有大的涵盖面。1985年10月26日,贾平凹在答《文学家》编辑部问时说:“他们(指拉美作家,笔者注)创造的那些形式,是那么大胆,包罗万象,无所不有,什么都可以拿来写小说,这对于我的小家子气简直是当头一个轰隆隆的响雷!”[3](P132)“我长期思考一个问题: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为什么能典型地概括那个时代的特点。我觉得是人家能够从现实生活中抓住当时时代社会心态问题,抓准了,抓得有力,涵盖面就大。”[3](P149)
进而,贾平凹认为,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应该借鉴西方文学的境界。“近代中国历史上有一句著名的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而发展的在文学史上只能借鉴西方写作技巧的说法,我觉得哪儿总有毛病发生。文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要阐述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反倒是我们应该借鉴的,无论古人与洋人。”[2](P17) “近年写小说,主要想借鉴西方文学的境界。”[4](P299)
贾平凹认为西方文学重在分析人性。在《〈病相报告〉后记》中论及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不同时,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文学的看法:
中国的汉民族是一个大的民族,又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它长期的封建专制,形成了民族的政治情结的潜意识。文学自然受其影响,便有了歌颂性的作品和揭露性的作品。……作品是武器或玉器,作者是战士或歌手,是中国汉民族文学的特点。
而外国呢,西方呢,当然也有这两种形态的作品,但其最主要的特点是分析人性。他们的哲学决定了他们的科技、医学、饮食的思维和方法。故对于人性中的缺陷与丑恶,如贪婪、狠毒、嫉妒、吝啬、哕嗦、猥琐、卑怯等等无不进行鞭挞,产生许许多多的杰作。越到现代文学,越是如此。[5](P303—304)
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贾平凹认为自己的创作应该分析人性,并且必须以民族的形式加以表现。他说:“如果在分析人性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氤氲,那正是我的兴趣所在啊。”[5](P304)
贾平凹认为西方文学采用焦点透视的方式叙述。“中西的文化深层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怎样写这个令人振奋又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我觉得这其中极有魅力,尤其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在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办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多有趣的试验!”[6](P6)
透视,指画家作画时,把客观物象在平面上正确地表现出来,使它们具有立体感和远近空间感。西洋画一般采用“焦点透视”,就像照相一样,观察者固定在一个立足点上,把能摄入镜头的物象如实地照下来,因为受空间限制,视域以外的物象就无法摄入。中国画的透视法则不同,画家的观察点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也不受固定视域的限制,而是根据需要,移动着立足点进行观察,凡各个不同立足点上所看到的物象,都可画入进自己的画面。这种透视方法,叫做“散点透视”。在小说创作中,焦点透视指作品围绕某个具体人物和某些具体事件折射社会氛围和时代特征,散点透视指作品以极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展示时代风貌和和生活全貌。
贾平凹对西方文学的上述看法是中肯的。西方文学始终具有很强的人类意识,表现出对人性、人类命运的关注和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因而具有了大境界。古希腊神话中已经蕴含着对人性的表现,宙斯的好色,赫拉的嫉妒,就是人性的反映。《十日谈》对人的欲望的展示,《伪君子》对人性虚伪的暴露,《欧也妮·葛朗台》对贪婪的表现,《罪与罚》对灵魂的拷问,《美国的悲剧》对主人公克莱德野心的描写,卡夫卡《变形记》对人性异化的揭示,《分成两半的子爵》对人性善恶的剖析,等等,无不显示了西方文学分析人性的深度。《神曲》对人类如何通往光明和至善境界的探寻,《浮士德》对生命价值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复活》对道德自我完善的追求,《罪与罚》对灵魂的叩问,《等待戈多》对希望的等待,《荒原》对拯救之道的求索,充分表现了西方文学的博大境界。而且,这些深厚博大的思想是以焦点透视的方法表现的。
贾平凹对西方文学的上述看法,使他的创作走出了“山地笔记”时代编写感人故事的狭小圈子,逐步走向关注人类生存、人类命运的博大境界。
首先,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自“商州三录”开始,一直在思考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文明、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等一系列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商州三录以散文化的手法描写了商州的古老风俗、纯朴民风、奇人异事、自然景观,表达了作者对自然的向往。《商州初录》里的《莽岭一条沟》描述了一个恬然宁静的乡村世界:十六户人家依山而居,自给自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争斗,没有倾轧,也没有生存的艰难,山沟提供着人们足以享用的一切。他们为过往的行人在门前放置茶水、提供吃喝。《商州又录》描写了一个“地也无名,人也无姓”的山野乡村生活情形,呈现了山民们本真的生存状态。久居城市的贾平凹,回到自然本真的商州,心灵得到慰藉,顿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舒心与惬意。但他却不得不承认,城市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早已吹进了商州世界,侵蚀了这个世界里的诗性,那个自然本真的商州已经悄然瓦解。在《商州再录》的“题记”中,贾平凹感叹“商州不是往昔的商州”。 [7](P211)此时的贾平凹只是以自身的艺术触角敏锐地感受到了自然被文明侵蚀的现实,并表现出自己的迷惘和失落。进入20世纪90年代,现代化步伐不断加快,乡村与城市、自然与文明、传统与现代的分裂日益加剧,贾平凹对此不仅感受深切,而且更加自觉地探索二者的关系,更加深入地思考各自的价值。《白夜》否定城市、否定现代文明的文化取向十分明显,表现出向传统的回归。《土门》真实地表现了传统被现代无情摧毁的必然命运,作者无奈而又理性地表达了回归传统的不可能。《高老庄》从城市人西夏的视角,既展示了传统乡村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又暴露了传统乡村文化的落后与野蛮,进而表达了作者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双重态度——既深恶痛绝,又依依不舍。在这一矛盾态度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接纳。阅读《高老庄》,“你能分明感觉到作家的情感倾向由原先的戒备城市转而为一定程度上的接纳城市,由原先的依恋乡村转而为一定程度上的排拒乡村。”[8](P279)《秦腔》真实地描绘了传统乡村文化走向衰落的严酷现实,表现了作者对传统乡村文化的绝望和挽悼。
其次,80年代中期以来,贾平凹小说的主题由对时代的关注转变为侧重于表现复杂的人性。《天狗》以天狗和师娘的爱情为主题,谱写了一曲男女主人公在生命本能与道德规范的冲突中痛苦挣扎的人性悲歌和人性美的赞歌。《黑氏》以农村妇女黑氏的三次婚姻爱情经历为内容,表现了山村妇女人性不断觉醒的过程。黑氏从与“小男人”无爱的婚姻中解脱出来,获得独立的人格。与第二个丈夫木犊结婚后,黑氏虽然拥有了与丈夫平等的家庭地位,但缺乏灵犀相通的爱情,因此与来顺私奔。贾平凹充分肯定了黑氏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在黑氏身上寄托了美好的人格理想。《远山野情》通过香香与吴三大的爱情,反映了生命的本真状态,表达了对人性美的探寻。土匪系列《美穴地》、《白朗》、《五魁》、《晚雨》客观地再现了商州土匪的生存和生命本真,逼真地呈现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透过贾平凹笔下的匪人匪事,我们约略可以了解‘逛山们’的传奇人生,他们貌似丧失人性和人之常情,实则在残酷、怪诞的人生追求、心理及行为模式的表象下隐藏着更真实、更疯狂、充满着畸形创痛的人性烙印。”[9](P22)等更是如此。《怀念狼》的主题似乎是保护生态环境,其实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背景下剖析人性的恶。商州雄尔川捕狼队队长傅山等猎人在禁猎时代患上了各种奇怪的病,他们最终将商州最后一只狼杀死而全雄尔川人变成了人狼。小说通过狼性和人性的比较,凸显了人性的凶狠、残忍。人为了金钱,在活生生的牛身上一刀一刀地割肉;大人为了讹诈钱财,把自己的孩子推向行驶中的车辆;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意处死其他生物。《病相报告》以胡方和江岚的凄美爱情为主线,全方位地报告了时代和社会的病相,在读者眼前呈现了人性被践踏、被摧残的悲剧。中篇小说《阿吉》塑造了一个无赖小人阿吉形象。他没有成就大业的才干和智慧,却不肯也不安于诚实劳动。最擅长的本领是利用自己的口才作践糟蹋别人。小说通过阿吉形象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人性中的嫉妒、卑劣、无耻等缺陷。
《废都》是具有文化批判和人性反思多重主题的境界极其博大的作品。对《废都》的评价尽管仍有争议,但它所蕴含的文化批判和人性反思主题是不争的事实。“废都”既是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更是传统文化的缩影和象征。这里有不时可以捡到的秦砖汉瓦,落入寻常百姓家的唐代桌椅、香炉,曾是簪缨之族故居的残破院落,这里的人们喜爱古传散丸、秘制膏丹,相信占卜之术,喜欢谈禅论佛。生活在“废都”中四大文化名人——庄之碟、阮知非、汪希眠、龚靖元,无法摆脱因袭的传统文化的重负,无力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深陷心灵痛苦和精神绝望而无力自拔。尤其是作家庄之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圈子里找不到灵魂的栖息地,最后借自己的名气在异性身上寻找寄托,于放纵情欲中寻求灵魂的慰藉。最后在离家出走时死在火车站的候车室。而这些文化名人正是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文化精英”。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绝望。与此同时,作品让我们看到,在物欲膨胀的时代,灵与肉的分裂,生命力的枯萎,人性的失落。“废都”不只是文化废都,更是精神的废都,灵魂的废都,正如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因此,《废都》是以性为切入点透视传统文化和人的灵魂的高境界大作。
贾平凹在借鉴西方文学的境界、表现人类相通的上述世界性主题时,坚持运用民族的艺术形式,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10](P26)”其突出表现是写意手法的运用和散点透视的叙述方式。
贾平凹说:“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抽象而丰富,正是我求之而苦不能的啊!”[11](P7)清楚表明了他对写意的追求。这一追求具体表现为对意象的热衷。早在创作《浮躁》时,贾平凹就表达了这样的艺术追求:“我欣赏这样一段话,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6](P6)《浮躁》中“浮躁不安”的州河正是象征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心理和情绪的意象。《废都》中的埙、哀乐、牛、鸽子、大熊猫都是有着深刻蕴涵的意象,甚至收破烂老头反复喊叫的“破烂喽——!破烂喽——!承包破烂喽——!”也是意象,而“废都”的意象性更是显而易见的,它“象征了秩序、权力和文化的颓败”。[12](P259) “《白夜》是贾平凹意象用得最繁密、最贴切的小说。”[13](P333)题目“白夜”就是贯穿全篇的意象,它既暗示了主人公夜郎和虞白的鲜明差异,更象征了没有白天和黑夜之界线的颠倒混乱的现代城市。小说的意象从物象发展到人物,甚至许多情节都成了意象。比如,再生人的钥匙、虞白的古琴,颜铭的豁嘴婴儿、再生人,夜郎用再生人的钥匙去开戚老太太的门、夜郎患夜游症、改编的精卫填海的寓言故事,等等,这些物象、人物和情节都是蕴涵丰富的意象。《高老庄》整部小说都在追求一个大意象。作者在《〈高老庄〉后记》中说:“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是什么,我的初衷里是要求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行文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14](P415)书名“高老庄”,主人公的名字——子路、西夏,双腿残疾的石头,画像砖和白云湫,等等,都是作者精心建构的意象。《秦腔》意象性更强。题目就是一个整体意象,引生这个人物也有大量的意象,夏天仁、夏天义、夏天礼、夏天智等人名也有意象性,白雪生下的婴儿没长屁眼、秦腔一步步走向衰败、夏天义七里沟淤地等情节更是富有文化隐喻的意象。正如平凹自己所言:“局部的意象已不为我看重了,而是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15](P658)
散点透视的叙述方式贯穿于贾平凹自“商州三录”以来的创作始终。“商州三录”、《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等,都是用散点透视的方式叙述的。在这些作品中,贾平凹从不同的观察点表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例如,商州三录以移步换景的方式叙述了商州的风土人情、地理山川,《秦腔》通过白雪的悲剧、夏家的衰落、秦腔被流行歌曲取代、老一代农民的土地崇拜被新一代农民的金钱崇拜替代表现了清风街的变化和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总体而言,贾平凹小说的叙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如行云流水,不讲究起承转合,于当止处戛然而止,这正是他运用散点透视叙述的结果。
贾平凹在其西方文学观的主导下追求文学大境界和民族形式的结合,使其创作达到了以独特的民族形式表现世界性主题的审美高度。毋庸讳言,贾平凹在这一艺术追求过程中,有得也有失。例如,在追求意象的多义性时呈现出含混神秘,使读者如坠云雾,不知所云;在散点透视的叙述中,过分看重细节的价值和魅力,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而且有些细节常常重复出现于众多小说,如猫钻烟囱、老鼠掉入面袋子、鸡啄食人吐出的浓痰等。但是,他的西方文学观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艺术探索,对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具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孙见喜.贾平凹前传·鬼才出世[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2]贾平凹.四十岁说[A].贾平凹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4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4]孙见喜.贾平凹前传·神游人间[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5]贾平凹.病相报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6]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9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7]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5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8]肖云儒.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A].贾平凹研究资料贾平凹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9]张川平.匪事与人性[J].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1).
[10]贾平凹.我心目中的小说[A].贾平凹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11]贾平凹.卧虎说[A].贾平凹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12] 旷新年.从《废都》到《白夜》[A].贾平凹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13] 张川平.贾平凹小说的结构迁衍及其意象世界[A].贾平凹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14]贾平凹.高老庄[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
[15]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15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为商洛学院语言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商洛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