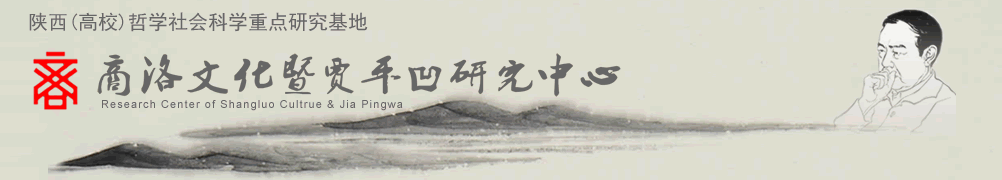张文诺
从广义上说,小说就是一种历史的表达,只不过是以历史上或许并不存在的人物名字来演绎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事件。“所有的诗歌中都含有历史的因素,每一个世界历史叙事中也都含有诗歌的因素。我们在叙述历史时依靠比喻的语言来界定我们叙事表达的对象,并把过去事件转变为我们叙事的策略。历史不具备特有的主题;历史总是我们猜测过去也许是某种样子而使用的诗歌构筑的一部分。”[1]历史是对过去历史事件的客观、公正的记载,历史总是以文本的形式来呈现的,我们所说的历史,其实是记载历史的文本。“任何一个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不可能再度呈现在面前,人们能够看到的是各种不同的历史叙述。历史叙述表现为一种对于过去事情的组织、陈述和编撰。”[2]历史著作主要是记叙影响时代进程的重大事件,包括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过程、结果,叙事简明扼要历史也是一种叙事,如果没有历史文本,过去的历史是无法为我们所感知的。历史要求撰史者从客观公正的立场秉公直书,而小说家则可以加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色彩,可以从自己的立场去写。优秀的历史著作也有可能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鲁迅称赞说“恨为弄臣,寄心椟墨,感身世之戳辱,传畸人质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3]。而文学往往在历史所不感兴趣的小事件着手,挖掘决定重大事件的一些小事件,写出事件的复杂性,因而,文学往往比历史典籍更让人感觉到历史的真实。任何一个作家都有很强的叙述历史的冲动,都想让自己的作品具有史诗性品格。贾平凹是当代中国作家中介入能力非常强的一位,他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动。如果按照贾平凹小说反映的历史时代的先后来看,贾平凹的小说几乎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动轨迹,具有典范的史诗性品格。长篇小说《古炉》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国是如何发生的;长篇小说《浮躁》反映了上世纪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长篇小说《废都》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心理挣扎;《秦腔》反映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衰败趋势;长篇小说《老生》通过四个时期的片段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转折;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是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战乱生活的诗化反映,显现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些本质性特征,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生活深刻的人文关怀。
一、传奇中的历史
贾平凹生于秦岭腹地的棣花镇,他在秦岭度过了少年与青年时代,对秦岭有很深的感情。他虽然走出了秦岭来到省城西安,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秦岭,因为西安就在秦岭的脚下,秦岭是他的精神故乡。他是秦岭的儿子,他一直想写一部关于秦岭的书,为秦岭写一部传记、或者写一部《秦岭志》以安顿自己的灵魂,为此他多次深入秦岭腹地做了长期的、仔细的、大量的考察工作。然而,他没有完成自己的“秦岭志”,却搜集了很多关于秦岭的传说。“关于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4]这些传说更新了贾平凹的历史观念,丰富了贾平凹对历史的深刻理解。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通过两条线索讲述了井宗秀、井宗承兄弟爱恨情仇的故事,再现了秦岭腹地一个小小山城涡镇的兴衰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战乱中国的社会现实,揭示了频繁的战乱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折射了那段历史的混沌与复杂。小说以一位普通的女性陆菊人为主人公,她是一位贫苦农民的女儿,因为还不起杨记寿材铺的债务,被父亲卖给杨家当童养媳,陆菊人带着她的嫁妆“三分胭脂地”来到了涡镇,涡镇的兴衰历史由此开始。陆菊人是带着远大的志向来到涡镇杨家的,因为她带来了一块风水宝地,她相信这块风水宝地能给她的未来带来好运。她结婚之后不久,涡镇水烟店井掌柜遭到绑票后不幸死亡,井掌柜的二儿子井宗秀临危不乱,冷静地处理了他爹的后事,他碰巧将他爹葬于纸坊沟胭脂地里,并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外财。井宗秀眼光独特,租了岳掌柜十八亩地种笋子,经营酱笋坊,事业得以迅速发展,还请了大部分债务,赢得了涡镇人的信赖。陆菊人对井宗秀刮目相看,告诉他那块风水宝地的真相,激励井宗秀做出一番大事业,井宗秀非常感动,决心不辜负陆菊人的期望。土匪五雷进驻到涡镇,让涡镇人痛苦不堪。井宗秀巧设妙计除掉了五雷,并当上了69旅预备团团长。经过一系列斗争,井宗秀领导的预备团迅速壮大,成为西北第六军的预备旅,井宗秀升为旅长。井宗秀当上旅长之后,大力发展涡镇经济,涡镇出现一片繁荣昌盛气象。在井宗秀大力改造涡镇之时,他在家中被宿敌阮天保暗杀,预备旅红十五军团被消灭,涡镇被炮火毁灭成为秦岭的一堆尘土。
这部小说故事庞杂混乱,除了井宗秀、井宗承兄弟的故事之外,还包含多个小故事。既有涡镇人的故事,也有山里人的故事;既有地主富户的故事,也有农民佃户的故事;既有国民党的故事,也有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贾平凹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5]贾平凹面临的最大困惑是叙述立场的问题,贾平凹既没有站在革命历史小说的立场进行宏大叙事,以达到特定意识形态的目的,同样也没有从新历史主义的立场,完全解构、消解宏大叙事的合法性。贾平凹从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出发,以民间流传的轶事趣闻、偶然事件、异样事物、卑微或不可思议的情形或者民间故事为基础重新想象当年秦岭地区发生过的事件,呈现了全新的历史画面,重构与再构了我们的历史想象。《山本》把一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作为叙述重心,展现了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发展历史。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国民党的地方武装都是鱼肉百姓的帮凶,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没有什么战斗力,也没有什么优秀的人物。在《山本》中,国民党预备团的团长井宗秀有情有义,有德行、干练果断;参谋长杜鲁成忠诚老实,踏实能干。预备团教官平时训练极为严格,经过严酷的训练,每名战士都身怀绝技;预备团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多次战胜强敌;预备团对外剿匪保护涡镇百姓的平安,对内发展生产、兴建涡镇,促进了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山本》中对国民党地方武装的描写迥异于我们的历史教材、革命历史小说、影视剧对他们的塑造,还原了一段客观、公正的历史。
“进入到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整个社会向‘小康’转型,在‘告别革命’的社会语境中,一种趋于保守主义的‘新历史观’逐渐形成,并在社会上下受到广泛认可。在‘新历史观’中,‘革命叙事’被转化为‘欲望叙事’,革命斗争被解读为权力之争,革命的动机受到深刻的怀疑,革命的灾难性后果被深度揭示。”[6]井宗秀的故事连接的是涡镇的历史与国民党预备团的历史,那么井宗丞的故事连接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这是一段革命的历史。与革命历史小说相同,《山本》叙述了革命起源的合法性与必然性。秦岭地区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大部分山民非常贫穷,再加上天灾严重,赋税地租丝毫未减,农民不得不东贷西借,高利贷者趁火打劫,导致饿殍遍地,民怨沸腾。秦岭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得到了普通百姓的拥护,势力发展很快。秦岭游击队爱护百姓,不侵犯群众利益,两个游击队员抢劫银元,受到了井宗承的严厉惩罚;两个游击队员调戏铁匠铺的小媳妇,被绑在树上不给吃喝。他们战术灵活机动,反复无常,神出鬼没,声势一天一天壮大起来。小说也没有回避革命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游击队在革命纲领的指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具有相当的合法性,因为的确有为富不仁者。但是,游击队在打土豪的过程中,也存在滥杀无辜的行为。秦岭游击队严格按照阶级归属确定敌我:凡是地主富户都是反动分子,都是双手沾满劳动人民鲜血的人,都是革命专政的对象;只要是贫农、雇农,不问贫穷原因,都是革命依靠的力量。只要是富户、政府人员部分青红皂白,一律杀掉。革命历史小说总是揭露地主富户的为富不仁、先天的反动性、极端的罪恶,以此渲染农民革命的合法性。“无论这历史中有多少血污、暴行和不公正,都由于它是‘通向未来’的而堂而皇之地谅宥了:付学费、必要的代价、难免论、‘吃梨削皮总要带点肉’,等等。”[7]《山本》却对革命历史中的残酷性、血污与暴行进行了质疑与反思,井宗承为了筹集革命所必须的费用,出主意让人绑票他的父亲,导致井掌柜精神恍惚而淹死在粪池中。这本来是一个为了革命舍小家而顾大家的感人故事,作者却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写出了其中的残酷,表现了作者对于历来我们所宣扬的为了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的那种理念的质疑与反思。井宗承率领游击队在夺取一家大户的三杆枪时,开枪打死了不说“实话”的当家,后来听说真的只有两杆枪时,井宗承说了句“你不该死的……今早托生吧,来世别再当大户。”作者借井宗承的自责表现了对为了革命利益而可以滥杀无辜的批判。更为真实的是,秦岭游击队多次在战斗中误杀了普通百姓,秦岭游击队为了袭击保安队,误杀了路过的老婆婆祖孙二人。小说大胆揭示了革命队伍中的复杂矛盾,秦岭游击队与平原游击队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以后,平原游击队的宋斌成为军团的第一领导人,他与秦岭游击队的蔡一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蔡一风被抓,井宗承作为蔡一风的人被抓,阮天保公报私仇,借机除掉了井宗承。作者通过井宗承的忠诚革命却为革命所革命的故事敞开了为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小历史,揭示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曲折、复杂与混沌。
长篇小说《山本》在反映二三十年代的秦岭地区的战乱生活时,具有民间传奇的特征,它没有正面反映重大的历史事件,把重大历史事件置于背景,着重描绘重大事件中的小事件。《山本》小说选取了秦岭游击队的一些奇袭战、阻截尹品三去省城、护送首长去延安、解救失散的红军战士等富有传奇性的小事件,把当年波谲云诡的历史写得鲜活生动、有声有色、扣人心弦。民间传奇总是反映不为正史所注意的、被大事遗漏的、遮蔽的一些小事、轶事、传说、偶然事件,民间传奇是历史的下脚料,然而,民间传奇却比历史大事件更加生动、更加鲜活,可以反映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小历史,可以揭示历史的复杂与历史的本质性内容。贾平凹吸取了民间传说的部分内容,但又超越了民间传说,赋予其鲜明的现代意识,从知识分子的维度对历史进行想象与反思。“当代民间说史,可贵的也就是摆脱了这一大阴影,形成新世纪文坛上活泼健康的审美风格。”[8]井宗承是一位忠诚而优秀的革命将领,他早年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革命,经过多次斗争的洗礼,他成为一位身经百战、身怀绝技的革命将领,英勇善战的井宗承没有死于两军阵前,而死于自己人的阴谋诡计。阮天保心狠手辣、无所不用其极,却能整死井宗承、暗杀井宗秀,这真是历史的悲哀与无奈之处。“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9]小说《山本》真实地反映了那段悲壮而残酷的历史,给覆盖着层层尘土的历史扫去了灰尘,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让历史恢复了生命与体温,达到了对历史本质的显现:过去是现在的过去,现在是过去的现在。
二、战乱中的生活
长篇小说《山本》通过井宗秀兄弟的传奇故事,描绘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地区的战乱生活,反映了秦岭地区人民的生活状态与生活形式,揭示了痛苦与生命如影随形的关系。“我们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幸福;所以,总的来说,人的生命根本就不是造物主给人类的一件有价值的礼物。”[10]小说表现了秦岭地区人民的苦难生活,传达出一种博大的悲悯情怀。
长篇小说《山本》展示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人民的苦难生活,小说真实地描绘了秦岭山区人民遭受的各种各样的灾难。接连不断的天灾让百姓的生活异常艰难,连年的旱灾让地里五谷都不好好长,而蝗灾又让即将丰收的庄稼化为泡影,山里人无以为食,逃荒要饭的非常多,所有的饭店门口更是蹲满了拿着破碗烂瓢的,看见拿食物的就抢。比天灾更可怕的是人祸,天灾不一定形成灾难,而人祸一定会引起灾难。那些年,政局混乱,弊病丛生,出现许多豪杰强人。土匪与战乱是秦岭地区人民遭受的最大的人祸,五雷四处流窜,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百姓深受其害。战乱时,人如草芥,很多人无端失去了生命。有钱的富户因为有钱被杀,没钱的贫民因为拿不出钱被杀,有的因为反对政府被杀,有的因为支持政府被杀。小说《山本》所描绘的政局混乱、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折射了旧中国中央政权日趋内卷化的真实现实,天灾会引起人祸,而人祸又会放大天灾带来的灾难,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中央政权的内卷化导致了地方士绅武化与劣化,井宗秀因为自己的父亲井掌柜惨遭横祸而死,不得不回家独撑危局。井宗秀高大英俊,面目白净,是涡镇最帅的男子。他心思细密,行事果断,父亲的死亡逼得他不得不自立门户,他在经商方面表现了独特的眼光,他选择经营酱笋坊,获得了成功。土匪的突袭让井宗秀无处可逃,他只好对五雷敷衍应付。五雷的横蛮让他疲于奔命,也让他深受屈辱,他利用反间计出掉了五雷与王魁。他成为新成立的预备团的团长,在与阮天保争夺武器的斗争中,他目睹了斗争的残酷,逐渐变得心狠手辣起来,他从一个有情有义、同情穷人逐渐变成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军阀。他有意让王成进横征暴敛,无视自己的部下抢男霸女,纵容底下人扰乱百姓,他残忍地杀害了为他传递信息的孙举来。他设计把麻县长骗进涡镇,自己却独掌涡镇大权,完全架空麻县长,成为涡镇的独裁者。在二三十年代,由于军阀混战,中央政府软弱,各地军阀林立,地方士绅开始武化与劣化。“这些武化的精英缺乏前辈乡绅的文化资源,往往带有后起和暴发的色彩,因而手更狠,心更黑,更不讲究道德规则。”[11]他们完全凭借实力与武器与对手抗衡,所以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井宗秀小时候聪明灵秀,有正义感,他从小学画画,如果不是他父亲突遭横祸,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画匠,井宗秀从一个涡镇的保护者逐渐演变成一个扰民者。在这种演变过程中,他也深受伤害,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了一个没有性能力、没有人生情趣的非人,他的人生轨迹显示了一个人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悲哀与无奈。
小说以冷峻的文字描绘了众多的庸常生命消失的血淋淋的场面。井掌柜淹死在粪池里,土匪牛文治被点了天灯,过路的老婆婆祖孙俩被游击队员按在稀泥里憋死,桑木县保安队长被秦岭游击队打了七枪而死,桑木县县长与其他政府职员被集体枪决,土匪玉米被土蜂蛰死,岳掌柜被土匪用石头砸死,一些游击队员被黑熊与野猪吃掉,杜英死于毒蛇,梁伍被长矛戳死,井宗秀媳妇淹死在井里,土匪五雷被其部下王魁土匪掐死,王魁被保安队打死,财主周长安用油灌死,恶霸程茂雨被井宗承枪杀,阮天保的爹被砸死,阮天保的娘被吓死,货栈李掌柜跳城墙自杀,周瑞政、周作云等秦岭游击队员被铡刀铡死,秦岭游击队跌下崖摔死了六人,落石砸死二人,被毒蘑菇毒死五人,蔡太运患病而死,杨掌柜被大树砸死,陈来祥被钟砸死,三毛被剥皮,邢瞎子被剐死,革命群众张老仓的孙子被摔死,儿媳被打死,张老仓被打死,钱老大被勒死,有的百姓缴不起捐税喝老鼠药自杀。那个年代“军阀割据、秩序大乱,每个人都命贱得很,生来很随意,死也随意。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正面人物或者英雄人物死得特别壮烈,惊天动地,特别有意义。《山本》里死亡特别多,,而且死得都特别简单。但是,你想想,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没有谁死得轰轰烈烈,都是偶然就死了,毫无意义就死了。”[12]在小说《山本》中,贾平凹写了如此多的人的死亡,并且每个人的死亡形式都绝无雷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表现了作者对那个荒谬时代的批判与揭露。“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包含有人性骚动的所有内容,包括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文学艺术中会转化成对经典性的企求,乞求存在于群体或社会的记忆之中。”[13]小说描绘了人在面临死亡时的种种表现,展示了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表达了作者对漠视生命的行为极度愤慨。更为深刻的是,小说还揭示了生活的一种悖论,战乱时期,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如草芥,没有人会关心其他人的生死;和平时期,老百姓的处境并未得到真正好转,和平时期的统治者往往大兴土木以炫耀自己的政绩,这需要从老百姓身上大肆搜刮,老百姓的生活仍旧非常痛苦。井宗秀打败阮天保之后,涡镇获得难得的和平生活,涡镇的经济有了发展,市场开始繁荣,涡镇人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此时的井宗秀意气风发,大兴土木,改造涡镇。改造涡镇的街巷是必要的,但修建鼓楼与戏楼完全是一种好大喜功的行为,导致财政入不敷出,他们向全镇每户征收五个大洋,全镇老百姓叫苦不迭。赵屠户拒不上交被预备旅转了起来,关了禁闭不给吃喝。小说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战乱与和平的辩证关系,战乱是永恒的,和平是暂时的,战乱犹如连续播放的电视连续剧,而和平犹如电视剧间插播的广告。
不但如此,小说《山本》勾勒了庸常人生的可怜、可悲而又无奈的现实,揭示了庸常人生的可怜之处。借小说中陈先生的话说:“这镇上谁不是可怜人?到这世上一辈子挖抓着吃喝外,就是结婚生子,造几间房子,给父母送终,然后自己就死了。”[14]涡镇的人们善良而又自私,淳朴而又可怜,老实而又卑微,他们的愿望不高,要求不高,他们就是盼望能平安过一辈子。他们在和平时期苟安自足,一旦战乱到来,却又自顾自己。陆菊人巧妙地利用土蜂蛰死了土匪玉米,她的壮举赢得了涡镇人的尊敬,都在夸赞陆菊人。可是土匪头子五雷发现玉米失踪返回涡镇向井宗秀要人时,人们又都傻了眼,再不说了陆菊人的好,反而埋怨起陆菊人来。人们面对强敌时,希望有人站出来反抗,可是一旦反抗不成惹下了麻烦,人们便又失去了共同的牺牲精神,开始抱怨反抗者扰乱了自己的生活。“在现实主义作家们看来,一件艺术作品的性质,并不依赖于它的题材的伟大或渺小。没有任何题材不能被艺术的构成能力所渗透。艺术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能使我们看见平凡事物的真面目。”[15]贾平凹深刻洞察庸常人生的庸常心理,揭示了庸常人生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表达了一种莫名的悲哀。井掌柜突遭横祸,镇上所有的女人与男人都成了长舌妇,说什么话的都有。当别人有难时,他们暗自庆幸灾难没有落到自己头上,把别人的灾难当作自己的谈资。贾平凹冷峻地揭示了人性中的弱点,正是这种难以摆脱的人性弱点使人们遭受更大的灾难,人们要想走向更美好的生活,必须逐渐摆脱这种普通卑微或许有点阴暗的心理。
三、人间大爱的执着探寻
秦岭是横亘于中国中部跨越北方与南方的巨大山脉,是中国南北分界线,是长江黄河的分界线,是中国最伟大的山脉。秦岭是贾平凹的精神家园,他要为秦岭写一本传记。“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16]为了了解秦岭,贾平凹多次走进秦岭感受秦岭,感受秦岭的呼吸与气韵。其实,描写秦岭不在于描绘秦岭的外观,而在于写出秦岭的气韵与精神。
秦岭的气韵在于它那博大无私的胸怀。秦岭在中国中部绵延一千六百多公里,秦岭里边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有八百多种草和三百多种树。秦岭里居住着各样的怪兽怪鸟怪鱼,有长着羊角猪鼻的羚牛、会变成虫子的毛拉草、会笑的熊、会变颜色的狸子,有双头鱼、铁蛋鸟。秦岭里既有大山深处的山民,也有城镇的市民;既有英雄,也有恶霸;既有战士,也有土匪。不论是那种生物,都是秦岭的一部分,秦岭以宽大无私的胸怀给了他们的土壤、水分与滋养。在小说《山本》中,最能代表秦岭精神的是陆菊人、陈先生、宽展师父等三个人物形象。最先出现于读者面前的陆菊人是一位贫穷农民家的少女,因为父亲还不清债务被抵到杨掌柜家当童养媳,她要了一块风水宝地作为嫁妆,她本来想把自己的公公婆婆葬在那里以保佑杨家、为杨家带来好运。她勤劳善良,善于持家;她孝敬公公,体贴丈夫;丈夫杨钟不学无术、吊儿郎当,成天不在家,她任劳任怨,独立一人操持家庭,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她有极强的经营才能、甚至具有现代经营理念,她作了茶行总领之后,锐意进取、大胆改革,为茶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当井宗秀把父亲葬于那块胭脂地之后,她开始很生气,后来她了解到井宗秀的能力与品德之后,就激励井宗秀做出一番大事业,为涡镇人造福。她深明大义,多次劝说井宗秀改变错误决定,多次让井宗秀避免了更大的失误,也让涡镇人多了一些平安。阮天保攻打涡镇时,三个不明真相的妇女把她暴打一顿,她给预备团战士说那三个妇女不是内应;王成进采用强硬手段纳粮缴款,还抢人妻女,陆菊人劝说井宗秀撤换了王成进。井宗秀攻打阮天保的游击队,周一山把涡镇所有姓阮的人都看管了起来,陆菊人认为这样会适得其反,把阮姓人都推到阮天保那边了;井宗秀回来后,要杀掉阮氏族人十七人,陆菊人极力劝说井宗秀不要意气用事,井宗秀拂袖而去,陆菊人找到麻县长,让麻县长说服井宗秀改变错误决定;井宗秀要活剥三猫,陆菊人劝说井宗秀不能这样残忍,但没有成功,只好去130庙给菩萨上香为井宗秀赎罪;井宗秀在每家门上挂鞭子把很多女人召到屋院,陆菊人把井宗秀哄到纸坊沟她爹的坟上,苦口婆心劝说井宗秀改变错误决定。井宗秀召集演戏的演员唱堂会,陆菊人严厉地斥责井宗秀要其认清涡镇人才是预备旅的衣食父母。陈先生是涡镇的一名老中医,五十年前他跟元虚道长学医,二十年前的雨夜被拉去当兵,他目睹军界混乱,自己弄瞎了眼睛回到涡镇当了郎中。他是一位瞎子,他靠号脉为人治病,他技术高超,一般的疑难杂症都能治疗。陈先生能治疗头晕病、尿床病、感冒发热、月经不调、心脏病、胸闷病、不孕症等,为涡镇人解除了身体痛苦。其实,陈先生不但能治疗身体疾病,也能治疗心理疾病,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陆菊人的精神导师,陆菊人一旦有了不能解决的困惑,就到陈先生那里去询问。陈先生不但医术高超,而且还有一颗仁心,三合县凤镇发生霍乱,陈先生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前往,半个月后回来时,陈先生瘦得皮包骨头,头发都花白。宽展师父是130庙里的主持,她是个尼姑,又是个哑巴,总是微笑着,在手里揉搓一串野核桃,宽展师父为涡镇人诵经、吹竹八。宽展师父有同情心,并且很勇敢,勇于救助别人。井宗秀的爹井掌柜死了之后找不到地方埋葬,便浮丘在130庙。王成进抢来一户欠粮人家的女儿,宽展师父与陆菊人冒着危险一起帮助她逃出涡镇。陈先生为涡镇人解决身体疾病,而宽展师父为涡镇人解决精神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陈先生是元虚道长的徒弟,是道家子弟;宽展师父是一个尼姑,是佛家弟子,二人都是涡镇人离不开的最重要的人物。涡镇人每遇到重大事务,都要请陈先生与宽展师父参加。陆菊人与杨钟订婚,陈先生与宽展师父是证婚人。茶行开业,宽展师父吹奏竹八作为见证。陈先生与宽展师父负责解决涡镇人的生死问题,涡镇人有病了,去找陈先生;涡镇人有人去世了,就要去请宽展师父。很明显,作者在陈先生与宽展师父身上寄托了很深的寓意,陈先生洞察入微,却是个盲人,宽展师父能抚慰人们的痛苦,却是个哑巴。这反映了贾平凹对生活的深刻洞察与理解,有的人有眼却不一定明事理,有的人能言却未必说出真理。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7]欲望过多必然让人更加自私,丧失存在之初心。这三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作者对博大、无私的人性的呼唤。陈先生、宽展师父不单单是代表了道释两家的信条,而且是博大无私的人性的象征。陈先生、宽展师父不但有担当、有责任,而且还有博大、无私、宽厚的胸怀,土匪五雷死后,宽展师父也为他在庙里立了一个牌位,让他们的灵魂安妥。
这篇小说的结尾具有很强的隐喻意义,涡镇在炮火中遭到了毁灭,麻县长自杀,井宗秀、杜鲁城、周一山等多少英雄灰飞烟灭,成为秦岭的一堆堆尘土。留下的只不过是宽展师父、陆菊人、陈先生、剩剩、与陈先生的一个徒弟等寥寥几人。“陆菊人看着陈先生,陈先生的身后,屋院之后,城墙之后,远处的山峰峦叠嶂,以尽着黛青。”涡镇的多少英雄事迹都被黑河、白河的浪花中淘尽,涡镇的多少宫阙,都化为尘土,只有象征人间大爱的陆菊人、陈先生、宽展师父在炮火中幸存下来。长篇小说《山本》揭示了那个时代的残酷与荒唐,然而,作者并没有对人类的未来失去信心,他执着地寻找着生存与世界的意义。贾平凹“一个字一个字地征服了空虚,把那种无话可说的状态变为生存的表达。”[18]贾平凹心中的秦岭精神象征了一种博大、无私、包容的美好人性,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性趋向完善的过程。“对于根本的人性,要充满信任和自信,你要相信,符合人性的事情总是会得到别人的理解。”[19]文学作为人类的向善、向美的一种艺术形式,应该帮助人们揭示、认识美好的人性。“人类存在的意义,便在于对人性的寻找。”[20]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本》揭示了存在的根本意义。陆菊人、陈先生、宽展师父等三人体现了秦岭的博大胸怀,这三个人相同的精神气质是对人间的一种大爱,这种大爱正是秦岭之本的鲜活体现。不管历史如何变幻,不变的是人间大爱与美好的人性,这正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秦岭中。
参考文献:
[1]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77.
[2]南帆.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0.
[3]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5.
[4]贾平凹.山本·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523.
[5]贾平凹.山本·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523.
[6]王春林.历史漩涡中的苦难与悲悯[J].收获.2018,(春卷):296.
[7]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1.
[8]陈思和.民间说野史——读贾平凹新著《山本》[J].收获.2018,(春卷):288.
[9]亚里士多德.诗学[A].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60.
[10]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M].高修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80.
[11]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58.
[12]贾平凹.写那么多死亡是为了诅咒那个时代[N],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4-26.
[13]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2011:16.
[14]贾平凹.山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50.
[15]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17-218.
[16]贾平凹.山本·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522.
[17]宋学海主编.诸子百家[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80.
[18]张旭东.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03:9.
[19]钱理群.可以对社会失望,但对人性要有信心[EB/OL].http://www.sohu.com/a/229372825_100150511.
[20]孙郁.百年苦梦—20世纪中国文人心态扫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