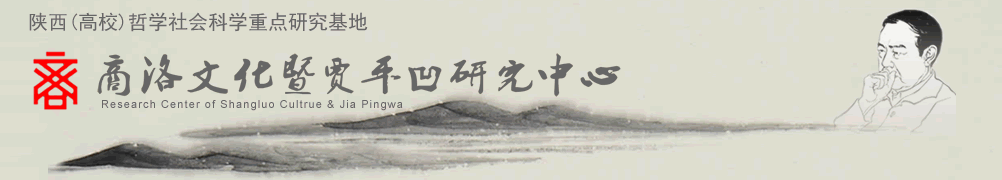张文诺 余琪
对于一部作品来说,它是否反映现实并不与作品的艺术成就成比例,然而,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无疑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与共鸣。对于一位作家来说,介入现实的能力似乎并不决定他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然而,深度介入现实的能力却是他保持旺盛创作力与艺术成就的关键因素。一部作品如果能发现别人所没有发现的层面,开掘出别人所没有开掘的内容,把生活的一些缝隙与角落表现出来,反映出别人所没有反映的主题,并能表现出人们的共同情感,那么这部作品无疑就是一部杰作。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贾平凹是一位介入感特别强烈的作家,他总是善于发现生活与时代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微末节,并从中概括出时代发展的主题性内容。“贾平凹从其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的生命体验出发,以中国当代人,主要是中国当代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为基础,来思考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生存问题,其精神中充满了忧虑意识,贾平凹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与当代人文化精神的不相适应,感知到了中国加速现代历史进程要求与发展过程对于生态环境破坏的矛盾,看到了现代文化发展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1]如果说《浮躁》准确地概括了转型期中国农村的一些时代特征,但失之于“实”;《废都》准确地预见了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然而失之于“灰”。长篇小说《秦腔》真实地描绘了现代性在农村的渗透与扩张,呈现了传统与现代在农村的巨大张力与矛盾。“传统与现代,新与旧,没有一种矛盾杂糅得如此让人无奈、揪心,而乡村又极容易主动或被动地卷入现代性的进程,极容易被置于制度与福利所弃之不顾的境地,被随意地规划与‘宰制’。”[2]长篇小说《秦腔》准确地反映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在现代与传统的纠结之中的社会变迁,呈现了后改革时代中国农民的思想、情绪、观念的状态与变迁,表现了作者对农村、农民的巨大关注与悲悯情怀。这部小说以白雪与夏风的情感纠葛为线索,展现了清风镇夏氏家族由盛转衰的必然趋势,揭示了当代乡村中国变迁的历史趋势,提供了当代乡村中国变迁的深刻而又生动的寓言,使我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缠中更好地感知与理解乡村中国。
一
九十年前,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以满篇“疯语”揭示了中国传统礼教吃人的本质,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以文学进行思想启蒙的书写传统。九十年后,贾平凹的《秦腔》以满篇“疯话”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深度描绘,揭示了中国农村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张力,呈现了当下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迁。
在中国农村,最本质的特征无疑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其间虽然经过多次外族入侵与多次社会变动,都没有动摇小农经济的根本地位。上世纪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水平的强行超越,结果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与经济的长期停滞。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应生产力水平的对传统小农经济的“回归”与“强化”,小农经济在新的历史时期又一次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显示了巨大的适应能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启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小农经济的弱点开始显露出来,愈益显出边缘化的趋势。长篇小说《秦腔》真实地展示了当代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趋势以及农村现代化步履的艰难与曲折,呈现了小农经济姗姗来迟的“黄昏”图景。小农经济式微的最明显表现是中国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恋土观念、安土重迁思想发生了变化。在清风街,享有崇高威望的老书记夏天义苦口婆心地教育清风街的农民热爱土地,可是愿意种田的农民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农民去城里打工,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抛荒。在清风镇未来发展道路上,已经下台的老书记夏天义与新书记夏君亭分歧严重,夏天义主张在七里沟淤地以扩大种植面积,夏君亭主张用七里沟换鱼塘,并建农贸市场发展商业以留住清风镇的农民。夏天义推动的七里沟淤地计划没有得到农民的拥护与乡政府的支持而失败,他的继承人秦安也没有办法号召农民支持淤地计划,与此相反,新书记夏君亭建设农贸中心的计划得到了农民的拥护与上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夏天义与夏君亭之争反映了下台书记与现任书记天然的、难以合作的心理,这也是传统与现代的理念之争、道路之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是夏天义在七里沟淤地的行为没有得到清风街村民的理解,只得到了他的孙子哑巴与清风街的疯子引生的支持。哑巴与引生都不是正常人,这预示了传统小农经济难以得到农民的支持。作者客观地揭示了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与落后性,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土地少、规模小,难以推行机械化,体力劳动繁重,生产率较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弱。“家庭农场规模过小,造成技术的退化,从机耕退到牛耕,从牛耕退到人耕,使机械化成为多余。”[3]再加上农业成本的增加以及农业费税的提高,农民在土地上的获得感不足,难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愿望,农民不愿意在土地上投入过多的劳动与情感。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发生了变化,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视土地、热爱土地,农民开始离开土地。现代化的本质而又显著的特征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工业化的结果是农业、手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向制造业相关的经济转变。不仅如此,工业化与都市化也在农村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至于农村变成了城镇、耕地变成了厂房。“当他们在家庭、农业经营和村庄的废墟上重建新的社会的时候,也就为农民的最后残存者敲响了丧钟……农民将在他们的伴随下自行地消失。”[4]小说《秦腔》描绘了现代性在农村的逐渐渗透、扩张,揭示了城市对农村的包围与渗透。
然而,现代化在农村的渗透过程不是一个轻松、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混沌、复杂甚至痛苦的过程。“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5]现代化在农村形成的深刻断裂让农村的老一辈农民感到非常痛苦,他们被抛弃了原来的生活轨道而感觉无所适从。农村现代化预示着传统乡村诗意的逐渐消失与乡村经验神话的逐渐破灭,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文学为读者建构了一种乡村经验神话。在传统文学中,农村是一个诗意的存在,那里没有尔虞我诈之徒,也没有勾心斗角之事,那里有轻松愉悦的劳动,有纯洁优美的爱情,那里是人们向往的精神家园。在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农民与土地形成了稳固的、富有诗意的关系。农民依靠土地就能基本保证他自己与一家人的生存与发展,他与土地及土地上的植物建立起一种诗意和谐关系。“人自己也因此变成了植物——就是说,变成了农民。他扎根于他所照料的土地,一种新的情感也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大地母亲(mother earth)。在播种与生育、丰收与死亡、孩子与谷粒之间,确立了一种深厚的关系。”[6]在中国传统农民的观念中,他不是耕耘土地,而是侍弄土地,不管地里有没有活计,他们总要到地里劳动才能感到心安,因为他认为他付出的劳动愈多,他的收获就愈加丰厚。只要不遇到巨大的天灾人祸,温厚的土地能基本保证农民的生活。对于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农民而言,他们的要求很简单,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内涵。简单的生活与淳朴的愿望形成了农村宁静、和谐的生活,面对乡村的安静生活,孟浩然写道:“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狭。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陆游称赞:“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在诗人们的笔下,农村不但风景优美,而且人性敦厚、民风淳朴。其实,这些画面是诗人想象中的农村,农民的真实生活是很辛苦的。李绅的《悯农》写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随着现代化的到来,工业经济相对于传统小农经济来说具有几何性的优势,从事工业经济的工人比农民收入高得多,在城市的市民比农村的农民生活舒适得多,而生活成本并不因为你收入低而减少,小农经济的劣势被放大,这必然会导致传统小农经济的衰落。五四以后,鲁迅先生的《故乡》最先揭示了小农经济趋于瓦解的趋势,茅盾的《春蚕》揭示了小农经济面临的困境。贾平凹把新世纪真实的乡村经验推到读者面前,展示了当下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
贾平凹对于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心怀忧虑,他深知农村的现代性进程不可避免,但从情感上对传统小农经济心怀不舍。值得注意的是,《秦腔》的叙述者是清风街的精神病人张引生,在清风街人看来,张引生是一个半疯半癫的思维不正常的人。小说通过张引生的眼睛,呈现了清风街很多难以为外人道的生活现象,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再现现实的清晰化手法,形成一种密实流年式的叙事,把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日常生活画面、日常生活对话“拼接”到作品中来,把农村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家庭矛盾、父子冲突、生产劳作、偷情养汉等琐屑甚至丑陋的片断呈现在读者面前,给读者以非常生动真实、可感的画面。“中国乡土文学的叙事方式都是以‘土地’的抽象化和符号化为手段的,‘乡土’的被‘悬置’常常使‘乡土’被遮蔽,无法呈现自身,最终变成了暧昧的工具性的存在。这两点其实也正是中国的乡土叙事虽然传统悠久、规模庞大,却似乎总是令人失望地无法触摸到中国乡土经验的本质和内核,总是给人‘不及物’之感的原因。”[7]因而,乡土文学呈现的乡村总是虚构、想象的,而《秦腔》呈现的中国乡土经验却给人很坚实、亲近的感觉,让读者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体验当下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并消解了乡土文学赋予乡村的美丽、宁静的牧歌情调,揭示了农村诗意生存的虚妄。
二
不可否认,随着小农经济的逐渐式微,附着在其之上的传统伦理也逐渐丧失传统的影响力与教化力。在传统社会中,调整人们之间关系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传统伦理宗法制度,传统伦理讲究父慈、子孝、妇从。在父/子、夫/妇这两对关系中,前者优于后者,后者低于前者,因而传统伦理又着重强调子孝与妇从,对家长的“孝顺”就成为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必然义务,同时也成为衡量家庭成员善恶与否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家庭不但是一个血缘关系集体,而且还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一旦家庭不睦,就会危及整个家庭的利益。“‘家’是农耕社会最为稳定的联盟单位。‘家’的范畴——包括家族、姓氏以及姻亲关系——包含了巨大的动员能力。”[8]维持家庭和睦的重要方式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必须服从家长的命令,所以传统大家庭特别强调儿女的孝顺。只要儿女孝顺,这个家庭就能保持基本稳定得以发展,否则,这个家庭就有可能瓦解。
传统伦理特别重视“孝”,忠孝乃立身之本。“只有人类才能意识到先祖(包括父母)是自己生命的直接来源。禽兽不记得父母祖先,这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所在。这个看法在古代很普遍,汉代的人大致都抱着这个信仰,因此自汉代起,中国人特别重视‘孝’。因为生命虽推源至天地(如西方的‘上帝’),但每个人的生命又直接出自父母和先祖。”[9]在清风街,做人成功的标准是他们的儿女孝顺、家庭和睦,然而,传统伦理在清风街已经日趋瓦解,每天都有置气打架的,常常是父子们翻了脸,兄弟间成了仇人。在清风街,只有夏氏家族还保留着传统规矩,夏天义夏天礼夏天智一辈子没吵闹过,谁有一口好的吃喝,肯定是你忘不了我,我也记得你。每到春节家家轮流吃饭,尤其是大年三十晚上,形成的规矩是:夏天义弟兄几个先到大哥夏天仁家,然后再依次到夏天义、夏天礼、夏天智家,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从表面上看,夏氏兄弟的感情非常好,家规非常严,然而,夏氏家族的规矩却显得非常僵硬与表面化,流于一种多余的形式。家规的僵硬说明夏氏兄弟平时根本没有在一起吃过饭,为了显示兄弟情义,有必要在春节那天集体吃饭,根本不考虑这样吃饭的不合理之处。夏天义虽然很讲究规矩,但对自己的家庭却没有任何办法,夏天义的几个儿子儿媳非常不孝,他们因为赡养问题而矛盾重重,甚至大打出手,让非常看重面子的夏天义很没有面子。夏天智诗书传家,讲究父慈子孝,然而儿子夏风对他并不顺从。夏天智喜欢秦腔,夏风最不喜欢秦腔;夏天智非常看重儿媳白雪,夏风却对白雪比较冷淡,夏风不经他同意就与白雪离了婚。
在现代社会,社会变动较快,原先的权力结构容易受到冲击。“如果社会变动得慢,长老权力也就更有势力;变得快,‘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就会发生,长老权力也会随着缩小。”[10]在清风街,夏天义、夏天智兄弟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夏天义自恃自己威望高,工作能力强,是清风街不可替代的当家人。然而他竟组织老汉老婆们挡修国道,被乡政府撤职。夏天义鼓动一些人反对君庭,也没有成功。在与书正发生纠葛时,书正一家闹得他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夏天义不但在清风街没了权力,在家里也失去了威信,几个儿媳妇都不是省油的灯,都不孝顺。夏天义不想依靠他们生活,一个人种点地,还要给每个儿媳妇干点活。他的几个儿子因为养老问题矛盾重重,大儿媳妇淑贞因为迁移坟墓的事与小叔子瞎瞎吵得不可开交,骂得不堪入耳。因为夏天义要拿八仙桌子与李三娃换手扶拖拉机,庆玉与夏天义激烈争吵,夏天义气得把八仙桌子劈成了碎木片。夏天义给几个孩子讲述祖先的发家史,遭到了孩子们的嗤笑。夏天义让孩子们来七里沟淤地,结果孩子们去了几天就再也不来了。书正的腿摔伤之后,夏天义的五个儿媳都不出钱赔偿,夏天义哭得老泪纵横,难过得自己打自己的脸。与夏天义不同,夏天智不怒自威,他在清风街民间社会的确具有相当的权威。村里有什么大事、矛盾都请夏天智主持或解决。夏天智虽然在清风街民间社会很有权威,但在清风街的公共事务之间,他的权威却不如夏风。夏风解决了夏中兴官职的晋升问题,夏中兴对夏风毕恭毕敬,夏中兴一句话就解决了清风街农民的土豆的销售问题。夏风一来,清风街的人们对夏风是毕恭毕敬,都央求夏风为自己办事,夏天智也央求夏风为自己出书。在年终风波中,警察抓住了八个人,夏风来了,乡长、乡党委书记为夏风接风,当下就把竹青放了。夏天智央求夏风去给乡上、县上说说,把抓的人放回来,夏风上午去乡上说了,下午就把人提前释放了。夏风的威信在清风街又高涨了许多。他走在路上,一路上谁见了他都问候。夏天义、夏天智之所以权威不再,是因为他们所坚持的理念、伦理、原则已经与现代社会的理念、伦理、原则格格不入,他们所秉持的传统话语在现代话语面前显得非常不合时宜,所以得不到众人的理解与支持。
传统伦理在封建社会调节人际关系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到了现代社会,其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传统伦理讲究四世同堂,崇尚大家庭伦理,认为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住在一起能表现出一种和谐、团圆气氛。传统大家庭在形式上很美丽,内容上却很丑陋,在表面的和谐之下隐藏着重重的矛盾。曹雪芹的《红楼梦》、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家》、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路翎的《财主家的儿女们》等暴露了传统大家庭的腐朽与矛盾,大家庭文化不符合现代人的个性发展需要。夏家同样矛盾重重,今年不比往年,夏天智还是交代要按往年那样过。今年的春节虽然聚到了一块,各个小家庭却是想不到一块,各家都有各家的心眼,并不一心,生怕别人占了便宜,但又充面子,便闹得很不愉快。夏天智家里,来了很多人,几个老人坐着,晚辈的立在桌边夹那么几筷,连吃带喝一个时辰,这些媳妇们说些不热不冷的话,饭吃得并不热闹,吃完大家都走散了,表面的热闹之下隐藏着深深的冷寂。
在传统伦理逐渐趋于瓦解的同时,传统权威的影响力在农村也正逐渐缩小。在清风街最有权威的一个是夏天义、夏天智兄弟。夏天义的权威来自于他的政治地位与人格魅力,夏天义一辈子都是村干部,是清风街的政治不倒翁,土改时他分地,公社化时他收地,四清中他无事,文革时他也没倒,改革时他再给村民分地,办砖瓦窑,示范种苹果,他想干啥就干啥。政治上的资历为他积累了权威,夏天义的权威还来自于他的大公无私,他从不假公济私。清风街不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大麻烦都会去找夏天义解决。夏天智的权威来自于他的知识与人格魅力,他博学多才且乐善好施,他是清风街小学的校长,一有高兴的事请别人去家里喝酒。他乐于助人,资助狗剩的孩子学费。他每天早晨起得早散步,回来时就沿途摇一些人家的门环,吆喝:睡起啦!睡起啦!回到家就门窗打开,烧水沏茶,一边端了白铜水烟袋吸烟,一边欣赏挂在中堂上的字画。夏天智在清风街有权威,在夏氏大家族里也很有权威,夏天义的几个儿子、儿媳不孝顺,夏天义出面把他们教训一顿。夏天智是个读书人,平时可以为乡亲们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深得农民乡邻们的认可。“乡民们对读书人特殊性的认可成为习俗,成为一种内化行为。”[11]张八哥的堂兄弟分家矛盾难以解决,连中街组长都没有分成,但让夏天智给解决了,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夏天智拥有道德解释权与话语权,谁不听从夏天智的命令,谁就在道义上站不住。
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特别看重人情,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包括亲情、友情。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人们一年到头都在自己的地里忙碌,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外地活动,人们的活动范围很小,社会关系很狭窄,方圆十公里即是人们的活动范围,朋友关系、婚姻关系、买卖关系大都局限于此。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大多依靠邻居、朋友、亲戚之间的帮助来解决各自的困难,这是一种建立在劳动交换之上的关系,你帮我,我才帮你,农村人特别注意有数,如果别人帮了我,我不帮别人,就会被别人认为无义或者不地道。农民特别羞于谈钱,他们对西方社会的那种动辄以钱付酬的做法很不理解。中国人特别注意亲情、乡情,就是因为这是一种不用花钱的投资,这是一种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之下劳动力配置优化的一种方式,所以必须讲究一定的规矩。传统文化讲究规矩与礼数,注重人伦和面子,“人们习惯于在温情脉脉的伦理纱幕中生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完全情感化、伦理化。这种社会心理积淀的结果,是人们陶然于伦理亲情,钟情于对现实人际关系的把握,并从中获得心理上的满足。”[12]传统伦理重视亲情、宗法等可以增强人们之间的归属感与凝聚力,让人们感到亲情的温暖、故乡的温暖,但也会产生一个后果:容易漠视个人的需求与权力,容易导致对人控制的加强,不利于人的个性与主动性的发挥。“换言之,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典型的人情世界。在人情面前,人们常常可以牺牲原则、正义、平等、公正等,一切传统乡村社会具有明显的经验式特征,生产生活具有重复性、习惯性、习俗化的特征,各种经验、习惯、传统、风俗、礼俗、乡规乡约、家规家法等成为指导生产、调节生活的最基本方式方法。“在这样一个人际交往高度频繁、人情关系十分密切的日常世界中,人际往来既是秩序化的,有一套细密繁琐的等级规定,个体的身份、行为被伦理体系严格限定;又是单一的,共享着同一的价值观念,使得乡村共同体中的成员能够自觉维护这一‘超稳定结构’。”[13]在传统社会的农村,人们安于被设定的秩序,人们之间乡村共同体非常稳固。“一旦社会不再有一个神圣结构,一旦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不再立足于事物的秩序或上帝的意志,这些社会安排和行为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嬗变由人。我们可以重新设计它们,我们的目的是让它们产生个人的福祉安康。因此管用的尺度就是工具理性主义的尺度。”[14]而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心中的神圣结构逐渐解体,调节人们之间关系就是基于理性之上的尺度,传统的伦理宗法、家规乡约对人的约束就逐渐缩小了。
三
随着传统小农经济的解体,附着于小农经济之上的精神文化也失去了载体。土地主宰着人们的想象,也主宰着人们的娱乐方式,与小农经济适应的主要文化形式是民间戏曲。小农经济遵循着一种自然节奏,农民们按照自然的节奏耕耘、播种、秋收、冬藏,不紧不慢、不蔓不枝,清晰而自然。民间戏曲讲究起承转合,结构叙事非常符合这种自然节奏,人们感觉非常舒适。“自宋元以来,戏曲表演成为民间娱乐的一种主要形式(小说在民间主要是通过说书人来传播的,可以近似地归为曲艺领域),各个地方几乎都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戏曲剧种,在演化中相互融化,也不断分化。”[15]民间戏曲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每逢重要的节日或者重大的事件,农民都要组织戏班唱戏以宣泄自己的情绪,增加热闹气氛,婚丧嫁娶要唱戏,逢年过节要唱戏,集市庙会要唱戏,宗族祭祀也要唱戏。唱戏时,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到这里娱乐、休闲、会友、聊天,老年人轻松地欣赏戏曲以排遣生活的压力,年轻人充分地展示自己的风采以吸引异性的注意,孩子们尽情地热闹以舒展自己的天性,戏曲是农村人们的一种生命形式与生存方式。
长篇小说《秦腔》以“秦腔”为题目,揭示了传统戏曲所代表的精神文化面临的危机。在过去的农村,几乎每个大点的村子都有戏台。戏台是唱戏的场所,平时是农民娱乐的空间。清风街有一个比较豪华的戏楼,那里的人们都喜欢看秦腔。在小说中,清风街的人们在重要场合还是演秦腔进行庆祝,比如夏风结婚时,农贸市场开业时,清风街都举行了秦腔演出。然而,秦腔的往日盛况难寻踪影,夏风结婚时,听秦腔的人不多;酒楼开业时,听秦腔的人很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唱流行歌曲的陈星让清风街的年轻人很是痴迷,并让剧团的演员惊讶不已。夏天智不喜欢流行歌曲,说陈星唱的软塌塌的,吊死鬼寻绳哩,但挡不住年轻人的热情。秦腔剧团巡回演出,看戏的人还没有演戏的演员多。在清风街,喜爱、真正理解秦腔的只有夏天智与白雪,夏天智痴迷秦腔,在马勺上画秦腔脸谱,还出版了一本秦腔脸谱专著。当年夏天智受到红卫兵毒打,他想自杀,优美动听的秦腔给了他活下去的理由与勇气。白雪是县里新一代最优秀的秦腔演员,才貌双全,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她一心想把秦腔艺术发扬光大,然而她的丈夫夏风不理解她的选择,想把她调往省城转行;白雪参加秦腔巡回演出,也未能挽回观众。秦腔演员生计难以维持,只好沦为为红白喜事的吹鼓手。昔日唱秦腔的名角王老师今日人老珠黄,再无往日的迷人风采。
表演艺术家王老师,在接下来就登场了,但她是一身便装,腰很粗,腿短短的,来了一顿清唱。台下一时起了蜂群,三蛰一直是站在一个碌碡上的,这阵喊‘日弄人哩么!’他一喊,满场子的人都给三蛰叫好,王老师便住了声,要退下去,报幕的却挡住了王老师,并示意观众给名角掌声,场子上只有笑声没有掌声。
作者以反讽的语调描写王老师表演秦腔的场面,王老师是昔日演唱秦腔的名角,在当地有相当的影响。昔日的她,亭亭玉立,口吐珍珠;现在的她,没有戏服的勾勒腰身显得粗短,没有乐器的配合声音听起来粗糙。清风镇的观众对王老师的表演不满意,他们开始起哄,台上台下一时大乱,乱成了一锅粥。白雪说:“我也吃惊,那么多人爱听陈星唱的,下午街上人都挤实啦!”秦腔之所以不再受农村的年轻人喜欢,原因正如书中所说:“有人嫌都是那一板戏,几十年迟早听厌烦了。”“秦腔不再是新一代农民的生命体验,雄壮苍劲的秦腔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沦为替村民送葬的挽歌。”[16]秦腔就那些曲调,来回就是那些经典唱段,节奏也比较缓慢,无法反映现代复杂的生活,秦腔无法触摸到现代人复杂的心灵世界,难以为现代人提供温馨的精神家园。“一个艺术品种如此深刻地植根于地域文化,这往往意味着普遍性的匮乏。越是地域的就越是普遍的,这句话在许多时候近似于谎言。”[17]现代人喜不喜欢传统戏曲,并不是年轻人喜新厌旧的问题,也不是现代艺术竞争的结果,而是像秦腔那样的传统戏曲无法反映现代人的情感,那种慢节奏也难以适应现代人的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戏曲宣扬的往往是封建传统伦理道德,传统戏曲的主题不外乎忠孝节义、忠奸斗争、忠君爱国、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等,这些是一种变形的传统农家意识,因而受到老一代农民的欢迎。然而,现代农民的情绪、思想、观念、价值都发生了变化,秦腔难以捕捉到现代农民的思想情绪,秦腔与农民的精神发生了疏离,秦腔就逐渐失去了农民观众。与秦腔鲜明对比的通俗歌曲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清风镇的外来者陈星仅靠一两首歌曲就获得了清风镇年轻人的青睐,这让秦腔演员尴尬不已。通俗歌曲接通了现代人的心灵,反映了现代人在生活快速变换过程中的孤独感、焦虑感、漂浮感,传达了现代人复杂的情绪与心绪。新世纪以来,农村的小农生产方式与附着于其上的精神文化受到了巨大冲击,这是农村即将到来的变革的序曲。现代社会开始了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变,从帝王将相到普通人、从英雄到凡人的转变。这是一种“祛魅”过程。现代社会“肯定对人世间的爱情、幸福等的追求,重新肯定世俗的生活,要求人生的享乐和个性的解放,肯定现实生活的意义。”[18]清风街民间歌手陈星歌唱的就是对世俗幸福的渴望,传达了一种现代人难以名状的孤独感与漂浮感,让清风街的年轻人感到情感的抚慰与愉悦。
《秦腔》真实地呈现了转折时期中国农村的生活,揭示了中国农村、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痛苦与艰难,贾平凹以一颗悲悯之心表现农村、农民的深刻变迁。读《秦腔》这部小说,让人感到心灵的强烈震撼与悲悯情怀,传达出一种悠远的人生况味。《秦腔》格调高远,在形而下的写实中透出一种形而上的超脱境界,贾平凹意识到了存在的不完美,存在的不完美不仅指人,也指物,他揭示了由存在的不完美而生发的痛苦、困惑与困境。任何事物走向完美的过程,也是一个走向结束的过程,发展的尽头就是“坟”,这是一个深刻的、不可改变的二律背反命题。秦腔是三秦人民的精神寄托,秦腔构筑了三秦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三秦人们的乡愁所在。秦腔是优美的,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它不可能一直辉煌。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秦腔难以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它的受众愈来愈少,秦腔的式微显而易见。听秦腔的人越来越少,最能理解秦腔精髓的夏天智因病死亡,懂秦腔的引生是个疯子。唱秦腔的人已是美人迟暮,老一代秦腔艺人王老师人老珠黄,晚景凄凉,令人唏嘘。新一代秦腔艺人白雪才貌双全,艺术精湛,一心想把秦腔艺术发扬广大,怎奈生不逢时,壮志难酬。贾平凹揭示了一种美好的事物必将要灭亡的悲哀与无可奈何,表现了一种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反思传统中,就有不少思想家怀着对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眷恋,带着美化传统的想象批判现实。”[19]贾平凹对传统艺术的消失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他坚持现实主义的立场写了传统艺术必然消失的悲剧命运,又对传统艺术的消亡怀有深深的同情与遗憾,写出了美好的事物必然式微的缺憾之美。夏天义英武一生,晚景却非常凄凉。夏天智追求家庭的和睦、圆满,他最引以为豪的儿子夏风却违背他的意图离婚。存在的本质就是矛盾的,再辉煌的人生都难以避免暗淡的宿命结局,再杰出的人物都难以逃脱由盛而衰的结局,这是存在的形式与尊严,也是存在的最高意义与最大魅力之所在。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多次重大转折,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与土地合作化运动,八十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改变了农村的面貌。相对于二十世纪发生的变化来说,那几次都是外力的推动——来自于国家政策的贯彻,新世纪以来的农村转折却是静悄悄地进行,然而更为深刻与广泛,这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前工业时代的城市是农业海洋里的岛屿。它们跨越城市生活的异域而相互呼唤,而这些异域却不为它们的实践所动。”[20]当下,中国农村却在城市的示范下进行现代性转折,并引起了农村发展的断裂。农村的现代性转折吸引了众多当代最优秀的作家的广泛关注,莫言、刘震云、阎连科、李佩甫、余华、毕飞宇、刘醒龙等作家从不同视角奉献出了反映当下农村变迁的优秀作品。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以农民的视角呈现了农村正在发生的变化,揭示了现代与传统在农村的冲突与张力。“工业主义催生出来的现代大都市,却颠倒了农业乡村的主宰地位,它们使乡村成为社会的边缘并且依附于都市自身。都市不仅成为权力和经济的中心,而且还在一步步地引导和吞噬乡村的生活方式。乡村反过来成为现代都市的一个象征性的乡愁之所。”[21]应该说,现代农村必然要取代传统农村,这是现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这种转折却是痛苦的,因为,传统农村伴随着优美、宁静与诗意而消失的。“世界以本文的方式诗意地呈现出它的整体关系,而人的生存活动也将被安置在这一整体关系的座架之中。”[22]小说不仅仅是对生活的呈现,而且它还为人们的存在提供诗意化的解释。贾平凹的《秦腔》写出了传统乡村文化变迁的生动寓言,为乡村中国留下了永恒的记忆,也为现代中国保留了永恒的乡愁。
参考文献:
[1]韩鲁华.精神的映像——贾平凹文学创作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94.
[2]谢有顺.乡土的哀歌[J].文学评论.2015,(1):20.
[3]王义祥.当代中国社会变迁[M].上海:华东师范出版社,2006:74.
[4][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71.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6.
[6][德]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二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78.
[7]吴义勤.乡土经验与中国之心[J].当代作家评论,2006,(4):75.
[8]南帆.文化的尴尬[J].文艺理论研究,2005,(2):66.
[9]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7.
[10]费孝通.乡土中国[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84.
[11]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12]刘春.乡土、乡俗与乡愁:《秦腔》的风俗世界[J].文艺争鸣.2012,(10):35.
[13]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72.
[14][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程炼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6.
[15]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33.
[16]程华.商州情节 长安气象:贾平凹的文艺世界[M].西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200.
[17]南帆.找不到历史[J].当代作家评论,2006,(4):69.
[18]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
[19]陈晓明.不死的纯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8.
[20]克瑞珊·库玛.现代化和工业化[A].陈永国译.现代性基本读本[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499-500.
[21]汪民安.现代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41.
[22]张旭东.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2006.